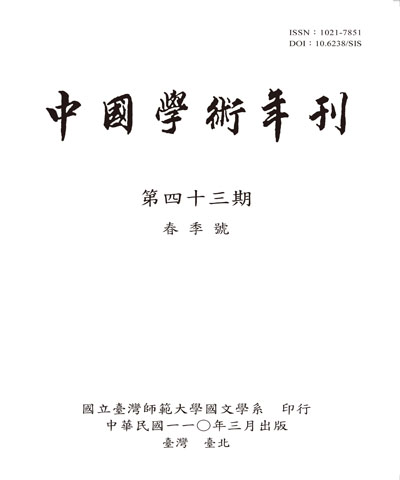
中國學術年刊/Studies in Sinology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小雅.斯干》中以「夢蛇」為生女之兆,可見遠古時虺蛇必被賦予強烈女性意象。筆者由神話、圖騰崇拜及古文物中搜集相關資料,認為此夢兆極可能源自遠古的蛇崇拜與女媧的始祖母形象。蛇的生命力、繁殖力與女媧創育人類的故事正切合先民對女性孕育功能的崇拜與嚮往,再經由神話、信仰的演變流傳,形成了〈斯干〉中的夢占。
- 期刊
吳澄對三《禮》的編纂以《儀禮》十七篇為經,仿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例,將《大戴禮記》、《小戴禮記》與鄭《注》分類編次,纂成《儀禮逸經傳》二卷。其後,再將《小戴禮記》六篇、劉敞補記兩篇及《大戴禮記》一篇附於《儀禮逸經》後,作為《儀禮逸經》之「傳」,又對剩下的三十六篇《小戴禮記》進行進一步的分類編次,編成《禮記纂言》一書。由此可知,吳澄對於三《禮》的編纂自有其一套系統的認識。《三禮考註》一書見於《四庫全書》存目,題為吳澄所著,然其真實性,自明代開始即有所懷疑,明、清諸多學者皆有所討論,然而所言皆未能全面性的辨明此書之真偽。本文擬就著錄與版本、體例與內容兩大方面加以考索,以期能對此書之真偽考辨清楚。藉由各種分析並與《禮記纂言》相照,以文字表達來看,《三禮考註》文字較為粗略,而《禮記纂言》文辭精當;就註釋內容而言,《三禮考註》註解較為簡省,且與《禮記纂言》態度明顯有所不同;就內容分類來看,《三禮考註》與《禮記纂言》、《儀禮逸經傳》多有不同,因此可以推論《三禮考註》一書實非吳澄所作。
- 期刊
戴震(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人,為乾嘉學術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的學問涉獵甚廣,其治學方法主張「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極深研幾,闡明經義。戴震對於名物度數的精核考訂,尤其以《考工記圖》一篇為時人所推重。戴震作《考工記圖》之目的是為了補足東漢.鄭玄(127-200)注的缺失,他在補注中逐一繪製圖象以作解說,於是古人制作的原意便昭然呈現。而《考工記》是因《周禮》中亡佚〈冬官〉一篇,乃補入之,於是《經》與《記》合為一書而得名。該書對古代社會裡諸多器物的種類、形制、構造、功用等均予以記錄,被視為一部古代工藝技術知識的彙編。對清儒而言,他們研治經學的方向不是從心性理氣作一形上思辨的論述,而是在經驗世界中關懷各種典章制度問題,並藉由考證方法的展開,重新安頓經驗世界的一切秩序。筆者發現自漢代以降的儒者對明堂制度的討論各有見地,聚訟不決,莫衷一是。是故本文擬以戴震《考工記圖》的明堂形制作為討論的中心。分為三個部分作說明:其一是論述《考工記》的明堂形制,其二是說明戴震對明堂形制的考證過程,其三是探討戴震考證明堂形制的意義。本文的論述欲以戴震作為個案研究,探討其研治禮學所運用嚴謹的考證方法,以彰顯出典章制度研究的思想活力。
- 期刊
〈隆中對〉之得失,海峽兩岸均有論文探究,臺灣學者主要把蜀漢不能復興漢室的責任,歸諸於關羽大意失荊州,此說過於直觀單一,難免忽略其他因素;大陸一些學者已注意到〈隆中對〉本身的缺失,唯諸說各有焦點,未能全面性探究此一問題。故本文主旨,乃全面性檢討〈隆中對〉之缺失。本文主張〈隆中對〉先天存在五大無解之難題,故雖有三分之功,卻無定鼎之業。知其得,則知其失;知其失,則益知其得。經由檢討〈隆中對〉之缺失,則更能體認諸葛亮卓越的眼光與智慧,能為當時尚無根據地的劉備,規劃一確實可行的建國藍圖,並導演半世紀餘的歷史走向。但由於外在環境限制,興復漢室本就是在不可能中尋求一絲機會,斷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 期刊
司馬光是宋代名臣,前人多注意他的政治影響及其史學鉅著《資治通鑑》。有關他的早年仕履,尚存疑點。司馬光將《古文孝經指解》獻給仁宗的時間,更是眾說紛紜。其實,《古文孝經指解》的書序結銜與進書表,均為後人留下關鍵線索。本文先釐清司馬光早年仕履的疑點,包括召試館閣校勘的時間,出任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的問題,以及赴任鄆州通判的時間。其次,本文將回顧前人對司馬光初進《古文孝經指解》的見解,探討各種說法的得失。最後,本文會以上述討論為基礎,利用書序結銜與進書表的內容,論證《古文孝經指解》初進於皇祐五年。
- 期刊
沈德潛雖未以格調論者自居,然學界多將他畫入「格調派」之畛域,然歷來學人對其詩學主張雖有不少精闢析論,但對「格調」之定義及所指並無統一。本文欲從當時詩學背景考量沈德潛教人為詩的企圖與手段,並推測沈德潛「格調」說之作用與內涵。並透過沈德潛之詩歌創作的觀察,進一步探求沈氏之用心與侷限。是知「格調論」在創作上固然主張摹擬前賢之格調,但主要理想是希望學詩人能藉此辨體之高下,進而從摹體之神髓而契合前賢,進而提升自我藝境,終能突破窠臼而獨自成體。沈德潛論詩最高陳義在於對第一等襟抱之完成,也可以說是向儒家傳統詩教回歸之詩論。然當時根柢不深又急求速成的學詩者,多只能達於摹體之階段,於變體、成體一無所識;因此「格調說」終不免流於優孟衣冠、畫虎類狗之譏。然其欲掙脫傳統的內省歷程,許多論詩意見深切獨到,對傳統詩學提供了反省的契機。
- 期刊
本文探討陳子展研究《詩經》的方法。陳子展重視歷代《詩經》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漢代學者及清代漢學家的說法。但是他不贊成《詩經》的教化作用,僅將此書視為文學和歷史的著作。由於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反省「詩教」被建立的過程,也試圖了解不同解說者的論證方式和階級立場,藉以解消《詩經》教化功能的神聖性。
- 期刊
「清談」是中古時期的一種特殊風尚,同時也是魏晉名士才情最集中的表現。「清談」不僅是名士的標誌,也是士人求官進身的敲門磚。「清談」影響了當代的哲學、文學、史學與美學;「清談」也是魏晉風度具體而微的展現。唐翼明先生所著《魏晉清談》,是一本獨立而全面地介紹魏晉清談的專書。之所以「獨立」,乃是因前人往往將清談現象混合著魏晉思潮、玄學、以至政治和社會等等來談論,而作者卻能當做一個獨立的歷史現象來處理。之所以「全面」,則是因為從來沒有人將清談做縱向、橫向全面式的處理,而本書不僅縱向地探討清談的起源、發展與演變,又能橫向地探討清談的內容與形式。《魏晉清談》可謂是研究魏晉學術、思想與文化者,不可不讀的一部書。本論文共分成如下章節:一、前言。二、《魏晉清談》之創見。三、對《魏晉清談》之建議。四、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