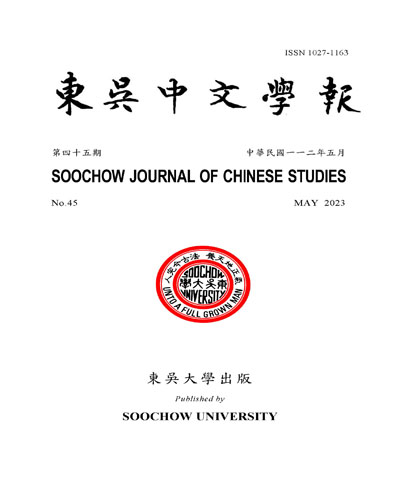
東吳中文學報/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遑恤我後」語見《詩經.邶.谷風》及〈小雅.小弁〉,自〔漢〕鄭玄(127-200)解「遑」字為「何暇」,後之注者多從鄭《箋》;實則鄭《箋》之外,尚有他解,如〔明〕何楷(1594-1645)釋為「急」,〔清〕俞樾(1821-1907)詁為「况」。經彙蒐相關資料對較,並從語境判讀,「何暇」之解雖多獲採用,實非的詁;俞氏之說,方稱允當。
- 期刊
《左傳》中屢見「諫」字,其義為「証」,「正言」也。其形式為居下位者向上位者進言,其內容「正言」,其所言意顯,其態度剛直,其所重公利。「諫」之深者為「強諫」、為「諗」。〈言部〉中若干字義與「諫」有部分交集,但或非正言,或嫌順悅,與「諫」義相去甚遠。《左傳》相關事例用「諫」字而非它,自當有意,或與書法有關也。
- 期刊
《史記》敘事最重要的特質在於抒情,藉《史記》抒情詠懷,是司馬遷獨特的「一家之言」,亦是《史記》突破先秦史書敘事表現之關鍵。〈刺客列傳〉為《史記》具代表性之名篇,其中豫讓、聶政、荊軻三傳內容與《戰國策》多所重疊,本文將二者文本相互參照比較,以具體突顯《史記》敘事之抒情性。不同於《戰國策》以敘述歷史「事件」為主,《史記.刺客列傳》敘事以「人物」為重,司馬遷書寫人物不但為傳主記功、為傳主立言、更為傳主「立名」-「刺客」在司馬遷筆下是為「知己」「捨生取義」之「壯士」,「士為知己者死」是刺客自我生命價值之實踐,亦是《史記.刺客列傳》貫串全文的主題。「士」與「知己」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士固為知己者死,但當「知己」對「士」並非真正的深知相惜,則「士」為其「知遇之恩」報之以生命,正顯現「士終不遇」的悲壯與蒼涼。幸而天地間,士仍有一二「真知己」,壯士終究不致真正孤寂。由於司馬遷對「士」與「知己」深有所感,《史記.刺客列傳》方能如此動人。而《史記.刺客列傳》之敘事結構,不論是紀年鈎連筆法,或「一唱三歎」的書寫形式,同樣展現出濃厚的抒情特質。抒情、敘事合而為一,是《史記》敘事風格獨特的重要原因。
- 期刊
七律是唐代近體詩的土產,也是唐代近體詩的寵兒,更是唐代近體詩的璀璨珍珠。考諸七律的誕生,初唐沈佺期作品,研練精切,已見工密。然盛唐諸大家除王維外,如李白、崔顥、王昌齡、李須、高適、岑參等人,所作不多,風氣未盛。七律詩體之振,當從杜少陵開始。子美雄深浩蕩、疾徐縱橫,允為顛峰,後再有繼者,僅得其一體而已!少陵七律,既用心會通前人創作經驗,又用意轉化成老杜風格特色,璀璨紛呈,百世嘆為觀止。筆者長期閱讀杜工部詩,略有心得,茲以其「會通轉化」技藝為文,就教於學者專家。
- 期刊
朱子強調讀書致知,並建立由經而史的閱讀途徑,然而學界對於朱子讀書脈絡之研究,多側重於《四書》閱讀次序的意義探討,對於朱子閱讀《五經》的程序則未有深入分析。有鑒於此,本文歸納朱子閱讀《五經》之言論,建構朱子《五經》閱讀次序為:《詩》、《書》、《禮》、《易》、《春秋》。並由此分別探討朱子讀書三階段的義理定位及價值,指出閱讀《四書》為學者建構本心義理的基礎階段,閱讀《五經》則為義理再次迴圈之深化階段,讀史乃至其他書籍則為義理運用階段。藉由此三個階段,朱子分別完成了上學下達再付諸應用的過程。經由本文分析,對於朱子讀書體系如何透過閱讀經學以完整獲取聖賢義理,並落實於運用的程程,當可有更清楚掌握。
- 期刊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眾多碑銘中有一類拓片十分特別,此類碑銘的題名為「後(后)碑」,可區分為後佛、後神、後鄉、後忌等多種。其中的後神碑銘,又有與生祠碑銘連用,或是同存並立的情形,呈現既有生祠又有後神的奉祀類型,為中國文化與越南民俗的融合展現。越南清化省東山縣安獲社鋭村的黎忠義生祠,即屬此種生祠碑記和後神碑記兼備的地方奉祀。安獲社鋭村為宦官黎忠義的家鄉,在其勢力高峰時,替黎忠義興建了此座生祠,祠左右各有兩方石碑,不僅為黎忠義一生事蹟之記錄,亦對鄰近各村社奉祀黎忠義為後神的原由與儀式加以記載,其詳列村社奉祀忌禮的組織架構與進行流程,足為越南特有的民族奉祀文化之例證。本文針對這四方共十面碑銘的拓片文字進行解析,對比銘文內容與史書記事的關連性,藉以說明碑銘對於史料的補證價值;再者從碑銘所記存的儀式內容,說明越南生祠與後神的奉祀特色,以為地方供祭之例證。因此研究黎忠義公生祠及後神碑銘,不僅得以一窺越南立後風俗之堂奧,對於中越文化關係,更能提供新的觀察角度,極富探查研究價值。
- 期刊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雲間陸氏儼山書院家刻刊行的《古今說海》,因「說選部」作品有詆毀夷風陋俗之論,因此清乾隆間纂修《四庫全書》時,除禁毀其部分子目書外,還對其違礙字詞進行改竄。由於文淵閣和文津閣本之改竄處及方式並未一致,甚至還有前後矛盾情形,知四庫人員評定違礙字詞的標準不一;在處理違礙問題時,或先釐清違礙字詞的內涵,至其改易方式,則只給予原則性的參考,是乾隆朝時禁毀情形之大略。然而道光間邵松巖重刊《古今說海》時,卻得能按照原樣雕版刊刻,這不僅因為漢滿逐漸融合後,民族歧視問題不再那樣敏感,對違礙字詞的敏感度銳減。且當時誨淫、誨盜的小說戲曲猖獗,為整頓世風、轉移人心,清廷查禁改以此類圖書為主。益以酉山堂採取影刻刊行,獲得版本學家顧廣圻的推薦,提供為《古今說海》的品質保證,同時得見清廷不同時期處理違礙字詞的差別。
- 期刊
孫德謙著《六朝麗指》,極力推崇六朝文為典範,以彰顯六朝駢文應有的地位,其中「氣韻」正是最為凸顯的美學特徵,也是全書文學論述的核心觀點之一。他不僅提出六朝文重氣韻的整體美感現象,也根據實際文例分析氣韻的創作重點及表現方式,頗見其獨特觀點,這對於六朝文章體貌的理解而言,當可有些許裨益。本論文首先針對氣、韻及氣韻的意義與觀念做簡要辨析,並探討氣韻所代表的文學特質;其次根據孫德謙的觀點,分析六朝文之體貌,以具體詮釋所謂「氣韻幽閒,風神散蕩」的特質;最後則探討氣韻與句式手法之間關係,如巧用虛字,穿插於句中調節,以添動宕之美;駢散兼用,活絡純粹駢體的僵滯體式,以暢疏逸之氣;潛氣內轉,使文理於內在的開合轉折中,依然銜承自如,故文氣自能疏緩而不迫促;另外則是利用斷字訣、岔入句、足句法、收縮法等,使語意表達更有迂迴曲折的效果,以曲盡抑揚之妙。凡此足見六朝文章頗具靈動、充滿生氣的一面,對於今日重新審視六朝文學的價值而言,甚有借鑒意義,而長期以來駢體過於重視形式而導致僵滯、冗弱之評價,也可藉以獲得進一步的釐清與理解。
- 期刊
清末民初,女小說家逐漸在文壇嶄露頭角,她們的作品,或者刊登在報刊雜誌,或者以單行本問世,也有的多次再版,引起不少讀者迴響。然而直到今天,這些女小說家的事蹟、作品,多數已經在時間的洪流中被沖刷殆盡,學界很少有人注意到她們,有一些研究者因而認為中國女小說家,要晚到五四時期才浮出歷史地表。資料的湮埋不彰,造成了現今學界的認知貧乏。事實上,清末「新小說」開始繁盛不久,女作家的小說便已經加入時代新潮,開始為婦女權益發聲,也殷殷以革新女界自期。當翻譯小說盛行於清季,女作家也很快加入這一行列,以小說翻譯為志業。當職業化現象出現在男作家身上時,也有女作家據此為業,藉謀生計。可惜現今學界,包括近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者,往往嚴重忽視了女作家的存在。資料的散佚寡存,也反映了學界與文壇一向重男輕女的慣習。本文選擇清末民初兩位女作家為題,嘗試運用有限的資料,勾勒她們的生平概貌,並藉由這兩位女作家為例,從中鉤稽女小說家的形成契機或因素,希望有助於揭開籠罩在清末民初女小說家身上的歷史黑紗。
- 期刊
西方從古羅馬時期拉丁文書寫定於一尊的時代,到使用地方語言,造成民族國家的興起,加劇現代化的進程。日治時期的臺灣,使用地方語言,有利於臺人族裔意識的凝聚,不利於殖民統治,則為政治的現實。因而臺灣文人與日本政府展開一連串的攻防措施與論述。臺灣文人盡全力要在現代化中完成自我與族裔形象的重塑,他們相信自己必須從文藝創作中尋找語言使用的方法,在這裡他們遭遇文言文/白話文、北京白話文/臺灣話文、日本話文/世界語等種種複雜糾葛的問題。什麼樣的語言使用可以協助他們邁入「現代」化的進程、而又保留「地方化」、「民族化」,抗拒日本政府的同化?或者是部分接受同化,保留「地方化」,向世界化邁進?本文分兩節討論臺灣文人對於語言使用從文言的漢文到白話的地方語、世界語的變遷,以及在這個變遷所產生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