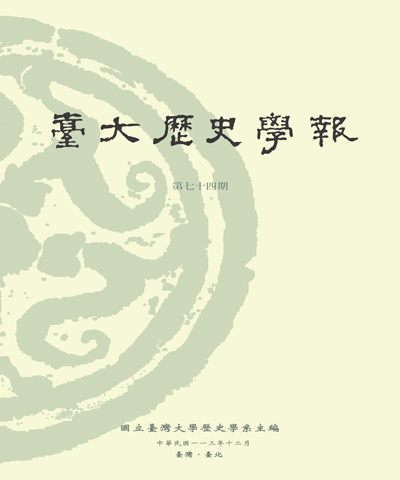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南宋的皇位繼承屢生糾紛,尤以理宗(1205-1264,1224-1264在位)的即位最具爭議性,由此引發的政爭影響深遠。當寧宗(1168-1224,1194-1224在位)垂死之際,在宰相史彌遠(1164-1233)的策劃下,理宗從原本的皇姪身分變成皇子,並順利承繼皇位。掌權的史彌遠隨即對內徵召理學名士入朝,對外強化控制山東忠義軍,企圖藉著新君即位,修補與異議者關係,創造改善政局的轉機。但是,寶慶元年(1225)年初,湖州爆發擁立失勢皇子趙竑(?-1225)的事變與忠義軍在楚州的叛亂,嚴重破壞主政者的佈局。為求穩定局勢,史彌遠逼死趙竑、全力安撫忠義軍的作法,引來諸多批評與抗議,最終導致史彌遠與真德秀(1178-1235)、魏了翁(1178-1237)為首的反對派徹底決裂,彌遠藉台諫官之力,將這批異議者逐出朝廷。理宗與史彌遠雖斥逐知名理學家,卻仍要提倡其所代表的學術來吸引士人的向心,以致真德秀等人雖失去官職,仍在民間著書、授徒,擁有極高的聲望。等到山東忠義軍的威脅在紹定四年(1231)大致解決,史彌遠放鬆對內的壓制,逐步恢復真德秀等人官銜與職位。只是經過這一段時期的激烈對抗,史彌遠與反對者的關係已難以修補,迨其身故,理宗親政,南宋政局仍繼續在支持與反對史彌遠的兩大陣營衝突中,持續動盪。
- 期刊
泰山做為華北重要的宗教聖地,進香者絡繹不絕,每年約有數十萬人,多時甚至達80萬。約在成化三年(1467),泰安州官員開始稽核廟宇香錢。其後官方將其轉入藩庫,並開徵入山香稅。為妥善收取入山香稅、檢查單據並掌管這筆收入,由泰安州以外的官員擔任總巡官與分理官,負責每四個月一次的監督任務。另外,為盤點廟宇的混施香錢,每年四月、九月的月底,又由總巡官與另一重新委任的官員會同打開殿門,清點信眾施捨的銀兩和貴重物品。這樣一個制度化的設計,在明代歷史上、甚至是中國歷史上,都是少見的。混施香錢與入山香稅,被稱之為泰山「香稅」,是個人捐款國家化、地方稅收中央化的重要例子,其運作規則較為完善,收入也最多。泰山香稅每年所收金額不一,16世紀約收到20,000至40,000兩,萬曆八年(1580)達到52,729.5兩。17世紀以後,官方所報數字逐漸下降,甚至僅6,000至10,000兩。按照規定,總收入的三分之二上繳,明朝後期大約上繳6,000至23,000兩之間。崇禎年間(1628-1644),遊客雖已下滑,但為應付軍費,仍須上繳20,000兩。至於留在山東省內的三分之一,其用途包括:補貼藩王、官員的俸祿,與救災、修廟、修城、修泰山的山道,及雇用差役、支應科舉考試費用等方面。自明末崇禎年間起,進香人數因華北寇亂及清初戰火連連而大減,但香稅上繳金額卻增至30,000兩;康熙中期,上繳數額降至21,205兩。雍正十三年(1735)廢除香稅上繳前夕,總收入才10,000兩上下。就總收入而言,清朝無法與明代相比,至於地方存留款,則主要用於科舉考試。
- 期刊
湯瑪斯.格林(T. H. Green, 1836-1882)是英國唯心論哲學傳統重要奠基者。相對於格林之政治關切,格林之宗教信念與神學思想相對較不受後代研究者重視,本文盼能彌補此方面之不足。作者企圖透過回歸19世紀宗教脈絡,重建宗教之於格林生命與哲學中之重要地位。第一部分首先考察格林所處時代及其信仰危機;第二部分追溯格林個人的宗教養成;第三部分主要透過格林著名的兩篇平信徒講道文,探討其神學觀及其所仰賴的唯心論哲學。我將指出,透過唯心論哲學,格林建立了一個超越證據、憑藉神聖意識且存乎於實踐之信仰觀。此信仰觀不但得以化解科學與宗教之衝突,重建道德實踐之熱情,並開拓一條超越教義、教派乃至教會等外在形式之寬廣信仰道路。
- 期刊
自1990年代以來,整合東德和西德的集體與個人記憶,一直是德國必須處理的棘手課題。對加害歷史的記憶,在公共領域中較為顯著;不過,關於德國受害的記憶也得到了更高度的關注。同時,歐洲逐漸成為在論及國家文化記憶時所參照的對象。這些發展受到種種後國家因素的影響,譬如歐洲化及國際化所帶來之不同層面的衝擊,以及多元文化在社會文化上產生的影響等。然而,記憶文化在德國也同時出現了一股再國家化(renationalisation)和正常化(normalisation)的強勁潮流。1990-2010年這二十年間,在記憶文化中,「他者」一方面得到了積極的肯定,卻也因為再國家化的趨勢而被排斥在外,相關研究者將這個過程稱為記憶的普世化(cosmopolitanisation)。本文從歷時性的角度評估1990年代以來,這種普世化的過程在德國關於二戰及戰後餘波的記憶文化中實際運作的初步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