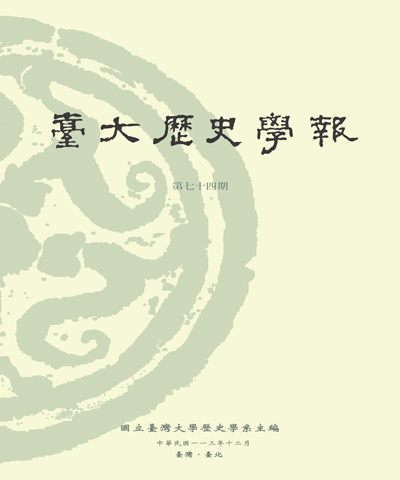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史家普遍認為北宋(960-1127)中後期是太學日漸蓬勃並最終壓倒國子學的一個階段。然而筆者研究北宋國子學的學制、教員編制和生員的出仕途徑時,發現在北宋晚期官學三舍法全面推行期間,貴冑子弟國子生的待遇遠優於平民子弟的太學生和辟雍生,由此可知國子學在北宋晚期曾一度復興,其為太學所壓倒並非單線發展的過程。儘管國子學反壓太學的傾向隨著官學三舍法的取消而破滅,但這種現象背離唐宋時期是從門閥統治過渡到賢人統治的認知,仍值得史家深思。一併考察國子學的短暫復興與同時期的銓試和恩蔭制度,筆者揭示蔡京等新進統治菁英如何利用這一系列優遇高級官僚子弟的措施,網羅親信和保障其家族的長遠利益。
- 期刊
本文由元代去思碑數量遠過於前代的現象出發,將文體視為一種文化模式,觀察去思碑產生的社會環境與行為,由此探索元代去思碑大盛的動力與意義。本文指出,元代取消唐、宋必須事先申請核准方可立碑的規定,一方面反映朝廷對頌揚文字管制的鬆弛,並影響當代建碑的風氣,另一方面也使得去思碑成為純地方性的事務,改變了建碑的意義。不過,制度鬆綁的影響只是一面,另一面則是蒙元新政治結構下的官吏士人群體對去思碑之名的追求與應用,是產生去思碑的主要動力。雖然去思碑不再是皇帝敕賜的榮耀,但其形式傳統賦予「循吏」之名的文化價值,卻在蒙元「後科舉社會」的新政治結構中發揮新的作用,成為一地官府與地方上層「士民」熱衷的活動領域。去思碑作為官員個人的資產,其應用存在於士大夫的網絡中。而作為地方紀念碑,在無需審查、大量出現的環境下,去思碑也成為地方人士參與政治行動的領域。對去思碑的應用因地而異,反映的是地方社會的性質。
- 期刊
杭州出身的獨立性易(1596-1672,本名戴觀胤,更名戴笠,字曼公,號荷鉏、天閒老人),自1653年58歲時東渡日本,至1672年逝世為止,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以儒、釋、道、醫的身分,在德川社會烙下其縱橫八千里路的中日文化交流足印。知名岩國儒士宇都宮由的(遯庵,1633-1709)稱獨立性易「為人博覽洽聞,涉獵儒書,出入佛乘,能書法,知醫術,最長者詩賦也」。而水戶藩儒小宅生順(1637-1674),則於記錄其至長崎尋訪碩儒經緯的《西遊手錄》中表示,「有學者,獨有朱魯璵而已」,獨立性易僅是「略解文字者三四輩」中的一人,二者評價相去甚遠。獨立性易身處中國時,正值明清交替、戰亂頻仍,勞碌營生但求溫飽;乘桴羈旅日本之後,苦難雖多,卻也得以展現個人才華。本文將獨立性易的生涯區分為鄉里營生時期(1596-1653),東渡日本後的尋求出路時期(1653-1654)、侍僧時期(1654-1658)、閉關時期(1659-1662)以及行醫時期(1663-1672)等五個時空,主要以在日本蒐集到獨立性易的詩稿翰墨之內容,循序漸進地探究其人格特質及思想轉化,考證獨立性易在不同身分、不同時空下的人物交流與事蹟,進而釐清其歷史定位。
- 期刊
清代臺灣史研究長期以來偏重陸地的農墾活動、行政統治和族群關係,相對忽略在綿長的沿海與廣大內海水域從事漁、鹽業活動的人群及其歷史。創立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時代,後經一定程度的改造與轉換,而持續被明鄭及清朝繼承的「港制度」,就是一個明顯案例。本文以位處臺江內海東北側、在明鄭及清代繳納港餉的「新港並目加溜灣港」為個案,具體分析「港戶」的水域權利,在清朝統治政策、社會發展以及自然環境變化交互影響下的演變發展。本文將具體說明,清政府在統治初期,將荷蘭東印度公司每年依競標制度出的漁場定額化,導致當時承攬港餉者得以「港戶」之名,長期控制水域。但因清朝官府改革稅收政策的著眼點,僅在於稅額的定額化,而不是制定一套完整的水域經營管理制度,因此港戶究竟擁有怎樣的水域權利,並沒有在港餉定額化的同時清楚劃定,而是在後來一再面臨官府的治理政策、整體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自然環境變動等因素,不斷地調整而釐清,才逐步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