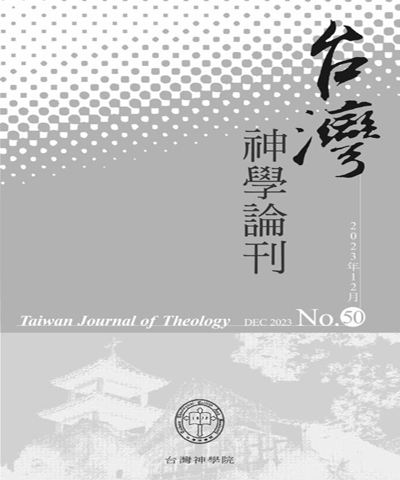
台灣神學論刊/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台灣神學院,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在過去四個世紀裡,加爾文傳統到底是如何在台灣島國發揮她的影響力呢?當「國際加爾文傳統」延伸到亞洲偏遠的一個角落時,它有展現出新的面貌嗎?本文旨在描述並分析台灣的加爾文傳統-實際通過荷蘭改革宗教會、英國和加拿大長老教會,以及剛成立且帶有本土自立特質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宣教工作-先後在荷蘭、晚清帝國、日本及國民政府統治下所呈現的四個範型。歷經時間的考驗,加爾文傳統在多元且富挑戰性的社會情境-初現代的殖民主義、家長式作風的現代化運動、戰爭體制下的試煉,以及本土化的民主化運動-裡留下恆久性的見證,並證明她具有微妙細緻的調適能力。
- 期刊
本文探討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1506-1564)的聖經解釋方法與特色。不同於中世紀的「四重意義」("Quadriga")解經法,加爾文強調經文字面意義(plain meaning)的重要性,注重經文的文字與神學的雙重意義。加爾文熟識歷代教父的作品,深信宗教改革家的理念,結合當時人文主義的語言學和修辭學,強調以「簡潔清晰」("perspicua brevitas")的原則來解釋聖經。此外,加爾文主張舊約和新約的連貫性,他在不同場合解釋聖經的作品逐漸發展成一套神學體系,其中尤其以《基督教要義》、聖經註釋、與講道集最具特色。這些著作處理經文的重點有些不同,但是其基本的模式與信息卻是一致。深入認識加爾文這些作品有助於我們瞭解加爾文聖經解釋的特色。最後本文以兩個實例(羅四章與創15:6;加四章與創十五、二十一章)說明加爾文如何解釋聖經,並思考加爾文的聖經解釋對我們今日的啟發。
- 期刊
本文討論宗教改革者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詮釋「信」所採用的「以知釋信」,以澄清知與信之間的關係,亦即理性與信仰之間的關係,並藉此釐清人文主義與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人文主義的精神可以以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 B.C.E.)的「認識自己」為代表,他認為真正的智慧使人認識自己的無知,這開啟了一條通往宗教信仰之路,而且他認為這樣的智慧本身是帶著神性的,如此「對自己的認識」就可能通往「對上帝的認識」。加爾文認為,「對自己的認識」與「對上帝的認識」二者息息相關,亦即知人知天與知天知人交織並行。他以「認識」為信仰的基調而以「知」釋「信」,甚至把信心定義為一種「知識」。本文從其親身經歷、思想方法追問信的知識之條件、特性、源頭與挑戰。表面看來,加爾文對信的詮釋帶有濃厚的知性色彩而傾向知性主義(Intellectualism),本文藉由帶有濃厚唯信主義(Fideism)色彩的存在主義思想家齊克果(Søren AabyeKierkegaard, 1813-1855)對信仰的反思作為其對照而探討如何分辨天人之際,從而觀察加爾文如何在知性主義與唯信主義當中取捨並如何在理性與信仰之間界定人文主義與宗教信仰的分際。
- 期刊
本文試著以《基督教要義》編排形式,從《基督教要義》第一卷第十三章論三一上帝、《基督教要義》第三卷、第四卷論到聖靈和聖靈工作的內容,分別檢視三一上帝當中基督與聖靈的關聯、聖靈在信徒信心和成聖當中的工作、以及聖靈在教會作為基督身體上的工作,包括聖禮當中的聖靈工作。對於聖靈在教會當中工作,特別採用加爾文講道篇和聖經註釋的材料,開展加爾文對聖靈工作運用在信徒成聖和教會生活的論述,從中發現屬靈恩賜、個人成聖和聖靈工作的關聯,作者由此發現加爾文聖靈論是以「與基督連結」為其核心主軸發展而成。
- 期刊
加爾文定義「上帝的話」(Word of God)包含三個面向:寫的(聖經),說的(講道),以及肉眼看得見的(聖餐)。換言之,「講道」在加爾文的神學架構中並不是單獨存在,而是與聖經作為上帝的啟示及對上帝的認識管道,以及與聖餐作為上帝恩典之媒介二者息息相關。若要更精確地掌握加爾文對講道的瞭解,就必須放在此一整全的神學架構下來討論,特別是三者之間的關聯性。本論文從三方面建構加爾文的講道神學:(1)為什麼需要講道?(2)講道與聖餐(3)聖經與講道,並進一步指出加爾文的講道神學是:講道是一種聖禮的行動,即在聖靈的工作下,講道成為一個人與上帝相遇並生命得到改變的歷史事件。今天再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講台的更新時,應該重新認識講道所具備的聖禮之特質。追隨加爾文的講道神學,今日改革宗的傳道人當相信並重申的是:上帝已經說話且在今日仍舊對人們說話,特別是透過聖經、講道與聖餐向人啟示祂自己。
- 期刊
本文針對加爾文的音樂觀點進行整理,以加爾文1536-1543年的著作為主要研究內容,並透過1539年加爾文第一本詩篇集《吟唱用詩篇與頌歌》("Aulcuns psaulmes et cantiques mys en chant")中二首由他所改寫的詩篇詞曲為例,以及法文日內瓦詩篇的內容與發展,來檢驗加爾文的音樂觀如何實踐在詩篇集中。
- 期刊
儘管約翰加爾文對於跨文化的宣教並沒有顯示多大的興趣,但是他所幫助過的諸多教會對於世界基督教的發展卻有重要的影響力。加爾文派的教會漸漸從本來是一個歐洲改革的運動,茁壯為一個跨越大西洋的新教運動,並於十九與二十世紀間,建立他們自己成為遍佈於世界中居少數的基督教運動。今日,加爾文派的教會一方面透過重要的普世教會組織像是「世界歸正教會聯盟」彼此聯合,同時也透過社會改造帶來了他們對其他教會的影響力。
- 期刊
這篇文章將探討約翰加爾文的著作與在歐洲的加爾文團體中有關人權觀念發展之間的歷史關聯,並且隨後試圖與在台灣的情境作某種聯繫。關於人權是首先在啟蒙時期與世俗理性主義影響下所發展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普遍主張是有它的局限性。反而,正如在早期歐洲宗教改革時期對宗教自由的追求,那樣對宗教自由的追求其實才真正為普世人權預備了更寬廣的教義發展與道路。而加爾文對教會與社區社會結構的獨特見解(介於路德與極端重洗派之間),與宗教改革精神所帶出的行動與模式都為人權發展播下苗床。儘管加爾文的著作在這個領域的重要性,但是它仍受到嚴重的局限,特別是受限於過於倚賴簡單與不全備的聖經觀點(如以十誡作架構),使得在處理多元性社群的問題上顯得不足。從上述的這些局限中鼓勵我們繼續追求普世的世界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