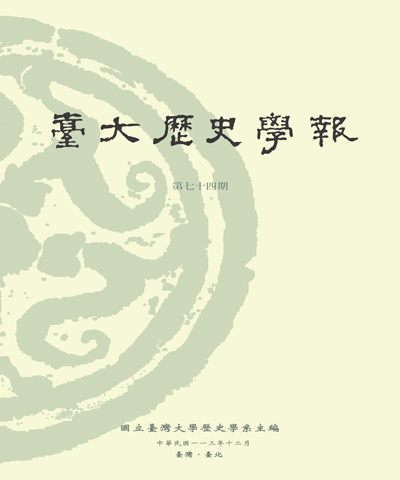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本文首先探討睡虎地秦律,指出戰國秦國在昭王(307-251 BC 在位)晚期設置十二個郡,當時郡並無權控制縣的人事;繼而根據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與岳麓秦簡《為獄等狀四種》,指出秦郡至秦王政即位(246BC)初期之後才掌有司法權,晚於縣與都官。根據上述及學界研究,可知昭王晚期以前的秦郡無權控制縣的人事、司法與財政,當時的郡縣關係可謂郡不轄縣。直到統一六國前夕,秦國方發展出郡下轄縣的地方行政制度。戰國秦郡在秦昭王晚期至秦王政即位之前,並未取得較完整的地方行政權,不宜視為在縣之上的地方政府。繼而,本文研究戰國秦金文,指出戰國時期自秦惠文王十四年(311BC)始,秦郡郡守便在縣工師之上監鑄兵器,反映郡的軍事性質。綜合秦簡與秦金文可推測,戰國秦郡郡守最早擁有的權力應為軍事權,取得司法、財政、人事等權力的時間晚於軍事權,由此可略窺戰國秦郡從軍區演變為地方政府的歷程。
- 期刊
帝制中國時期,孔廟從祀無論對於朝廷或士人,皆為不可輕忽之大事。唐代創立孔廟從祀制度,其判準主要為「傳經之儒」(經學學術成就),明嘉靖九年(1530)後始正式加入「明道之儒」(道德修養與德行表現)的選項。吾人易將嘉靖九年的重要轉變與陽明心學的發展相聯繫,但事實上這種提升「明道之儒」的努力,自明初以來便不曾間斷,並非陽明心學出現後才產生。早在弘治元年(1488),程敏政(1445-1499)已完整而具體提出藍圖及願景,並於弘治八年(1495)促成宋儒楊時從祀,首開其例。嘉靖九年孔廟從祀的全面革新,實本於此。明初以來,士人已關注從祀儒者的德行修養,隨著時間推移,其力度亦與日俱增。起先以「明道之儒」為證明某人不當從祀的反面例證,成化以降,始正面宣揚其從祀孔廟之正當性與必要性。程敏政集明初以來相關議論之大成,強調孔廟具有「垂世教、淑人心」的功效,故從祀儒者的德行表現遠重於學術成就。程氏據此要求罷黜鄭玄等德行不彰之經學大家,意圖樹立新的儒學典範。這些主張一方面與其「尊德性」為本、「道問學」為輔的學術信念有關,另一方面或因受到其連襟衍聖公廢黜為民的刺激。
- 期刊
明正德年間(1506-1521)以來大量興起的民間教派,如羅清(1442-1527)、殷繼南(1527-1582)、姚文宇(1578-1646)所統合的吃齋人教派,其實是在地方社會中提供宗教服務:包括處理生死大事、驅災祈福、娛樂及慈善互助的人群組織。是什麼「社會條件」促使這些民間教派形成?它的發展牽動哪些重大的歷史變化?這些非屬佛、道的民間教派,在常民生活中扮演何種角色?其所建立的「宗教家庭」,是否為地方社會「人群組織」結構性改變的關鍵因素?本文依序討論問題如下:首先,原生於北方的羅教如何轉變成流行於浙南、閩北地區的姚門教、老官齋教,乃至於之後的江南齋教?其次,這些民間教派的發展基礎與過程為何?最後,透過釐清姚文宇家族建立民間教派及發展過程,重新反省地方社會歷史發展與人群組織法則變化的相關問題。基於前人研究成果與實地田野調查,本文結合寶卷與族譜等民間文獻,還原浙江省慶元縣姚門教主姚文宇的家族歷史,並重新梳理明清以來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民間教派組織的發展過程,及其發揮的歷史作用。
- 期刊
本文欲由「建構論」出發,說明「害蟲」實為19世紀下半葉才慢慢在東亞出現的新概念和新語彙。以臺灣為例,後世被認為危害甚烈的「螟」蟲,雖然明清時期的文獻記載甚夥,但多半集中在轉化為比喻養子的「螟蛉子」風俗,而與農害無涉。今人或以為清朝無「科學」知識,故對蟲害無所知覺,然若執此一端,則輕忽了其間隱含的觀念變化。由「螟蛉」轉為「螟害」,正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將「害蟲」這個概念傳入後而來。近代國家的出現,殖民統治、都市化、戰爭需求,以及近代農學知識的轉型與應用昆蟲學的形成等多重因素的交會,才逐漸產生「害蟲」的概念。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時期,「蟲害」發生的頻率和種類不斷增加,實因應用昆蟲學讓原本早已存在於臺灣的昆蟲轉為害蟲。面對這些重新被界定、挖掘出來的害蟲,殖民政府透過制度的力量,包括頒布害蟲預防法規,設立農業試驗場、植物檢查所以及害蟲巡視員等組織,試圖防堵壓制「害蟲」對農作造成的損失。1920年代以降,日本化學工業突飛猛進,無機及有機化合物製成的農藥開始大行其道,臺灣的應用昆蟲學專家也不遺餘力地介紹各式新農藥產品。不過,農藥在不同農作物的應用情形並不一致,臺灣只有在柑橘瓜果等進入國際市場的農作物採取了「先進」的劇毒農藥,食糧作物中的水稻則仍維持傳統的人力防除法,而與日本國內廣泛使用農藥的趨勢不同,這或許是殖民地與母國在都市化及農業商品化速度不同的表現。
- 期刊
1947年5月,國共內戰中的山東戰場孟良崮戰役,國軍精銳部隊整編第七十四師被人數佔優勢的共軍圍攻,全軍覆沒。此役中擁有指揮權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1893-1987)誤判軍情,又忽略前線部隊準確的情報,錯失救援時機,是國軍慘敗的重要因素。相對於此,蔣中正(1887-1975)越級指揮與最高統帥部是否洩露情報,並非關鍵。國軍前線部隊執行作戰計畫的軍事行動之初,共軍已從戰場情勢中確認整編第七十四師的行動,祕密集結主力,伺機而動,在該師冒進、脫離與友軍互援後,切斷雙方聯繫。該師遭遇共軍強烈抵抗,撤至不利防守的孟良崮,又因顧祝同救援遲緩與友軍可能敷衍救援,導致該師被圍殲。在5月12-16日數日戰役期間,前線指揮官顧祝同比蔣中正更快獲得情報,也擁有下令部隊迅速馳援的指揮權,此是蔣顧二人的共識。該師撤至孟良崮的關鍵時刻,蔣中正仍樂觀以為此攻勢作戰可以殲滅共軍。然而,顧祝同的判斷錯誤,救援行動延遲一天,致使該師全軍覆沒。蔣雖在5月16日直接下達救援命令給各兵團與整編師,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