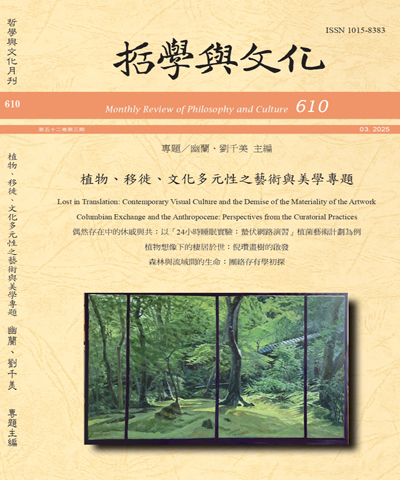
哲學與文化/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面對眾多的利瑪竇研究文獻以及他在各方面所做貢獻的定評,有關他媒介中西方哲學的會遇與認知,卻顯得較少有人做深入的關注和探討。作為天主教的傳教士,以士林哲學為正統的基督教哲學,當然是他所熟悉的哲學認知,但在會遇到陌生的中國「哲學」傳統時,他是怎樣理解這陌生的哲學呢?以及他如何讓這些陌生人理解他所要傳揚的、對中國人來講陌生的基督教哲學乃至神學呢?對此作者嘗試就利瑪竇自身的著作,從其教育背景及著重提出的論題來考察他在論述上的視野,同時也嘗試透過一種基於對陌生做回應的反思行動,或說是一種「陌生解釋學」,來對利瑪竇在媒介中西哲學上的貢獻做一些綱領性的探討。
- 期刊
本文透過版本的比較,介紹影響近代西方對中國宗教理解的一份極為關鍵的文本-明末耶穌會士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撰於1623年的《論中國宗教的幾點問題》及其後四種譯本之間的格式問題,聚焦在邊欄中文的考證與註釋的比對兩個方面。《論中國宗教的幾點問題》寫成之後將近八十年的時間裡,分別被譯為拉丁文(1661)、西班牙文(1676)、法文(1701)與英文(1704),在西班牙譯本正式出版後方逐漸廣為人知。其法譯本不僅是索邦神學院和羅馬教廷對中國耶穌會和中國禮儀進行宗教裁判的重要依據,此後學界的討論也多根據此譯本。不同時期的稿本和版本其格式和內容並不完全相同,箇中差異在於圖像、邊欄中文與註釋三個部分。圖像和邊欄中文僅出現在葡文原文和拉丁譯本,在正式出版的譯本裡均未見。而註釋為利安當和閔明我在翻譯時所加,龍華民的原稿未見,法譯本亦無,僅出現在拉丁本、西班牙文本和英文本。而西班牙譯本的注釋數量又高於拉丁譯本。本文將主要關注原文和譯本的格式,尤其側重在目前學界較少處理的葡文與拉丁文譯本,包含邊欄中文和註釋有無、刪增等問題。
- 期刊
在17世紀,大部分的耶穌會士及中國基督徒遵循利瑪竇的策略:排斥宋明儒學,用古代儒家思想解釋基督宗教。同時,另一些耶穌會士如龍華民等則反對利瑪竇的策略,認為古代及宋明時期的儒學都是無神論。衛方濟的《中國哲學》是很重要的轉捩點:他不接受利瑪竇所作的古今儒家之區分,與龍華民一樣強調儒家傳統的連續性,而且重新評估了宋明理學,並試圖在許多方面結合宋明理學與基督宗教思想。跟利瑪竇相比,這種儒家式的基督宗教哲學在形而上學上有更深的基礎。本文分析衛方濟如何克服前輩耶穌會士對宋明理學的排斥,並且說明他怎樣首次建立起宋明理學與西方哲學的共同基礎。
- 期刊
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婦女在教會中所受的專注逐漸增高,不少相關文獻相繼出爐探究婦女與瑪利亞,以及其與社會的關係。教宗保祿六世在梵二大公會議召開十年之後發表了宗徒勸諭「瑪利亞敬禮」、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1987年發表了「救主之母通諭」,隨後於1988年又發表了牧函:《婦女的尊嚴與聖召》,講述婦女的尊嚴與聖召是基督徒需要不斷討論的議題;1999年若望保祿二世訪問印度之際,更清楚地指出了瑪利亞的特色:她是慈悲的母親,交談與共融的母親,與亞洲教會關係重大。這些文獻顯示教會日益重視婦女所彰顯的瑪利亞形象,以及婦女對社會與教會的貢獻。事實上,談論瑪利亞形象對婦女的啟發,以及在她的影響下,婦女對天主教教會的貢獻,並非由梵二之後才開始,在梵二之前,或者早在早期傳教士來華之際,其實已有不少傳教士在其著述中討論瑪利亞的形象以及婦女對教會的貢獻。歷經漫長的歷史,瑪利亞形象的傳遞,理解與實踐,隨著時代的轉變產生了不同的可能性。本文擬嘗試由早期來華耶穌會傳教士柏應理《一位中國奉教太太:許母徐太夫人甘第大傳畧》、高一志《聖母行實》對於瑪利亞與女教友形象的闡述、梵二之後的教會相關文獻,以及當代女教友張秀亞在其文學著述中所描述的瑪利亞形象之互文對照,探究瑪利亞形象的典範移轉、接受以及此形象在中華語境本地化的過程中,對女教友的影響以及引領她們所做出的貢獻。
- 期刊
教廷為了更加瞭解中國傳教區的情況,於1919年7月22日正式任命廣州代牧光若翰(Jean-Baptiste Budes de Guébriant, M.E.P., 1860-1935)為教務巡閱使,並擬定一問卷,在他考察中國教務時訪察各方相關意見。他的行程自1919年9月15日至翌年3月12日為止。本研究鎖定該問卷中中國籍教士的地位以及擢升國籍主教兩議題,筆者透過光若翰呈教廷傳信部的報告中,爬梳受訪人就相關問題提出看法,另也分析各地國籍教士、修生和教徒多人主動投函提供的意見。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傳教士與國籍教士、教徒和光若翰本人對這兩項關乎中國天主教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之看法,以及他們之間意見異同與衝突點,探討在當時民族意識高漲的時代背景下,這些問題對整體中國天主教傳教活動、國籍教士和傳教士互動之影響,並找出問題癥結所在:許多西方傳教士傾向於固守舊體制,並懷有某程度的種族優越感。結論中,筆者指出教廷對相關問題與在華傳教士不僅看法不同,且堅持進行改革,支持並提升國籍教士的地位,以圖解決傳教士長期壟斷中國傳教活動造成的教會發展問題。
- 期刊
奧斯定對歷史的看法,在他的《天主之城》中詳細的表達,按他本人在序論中說,這是一部「艱難與龐大的著作」,是經過長期的沉思,將他的許多思想綜合成書,如一些琢磨的石塊般,構成宏偉的建築物。他從發生的事件,反思歷史的意義。奧斯定因對希臘文薄弱的知識,無法與當時的希臘神學家溝通,反而使他以創新的方法,為西方拉丁基督教會奠下思想的基礎,而他的創意,延續了希臘與西方羅馬教會的傳統。「天城」與「地城」是本書的重要概念,時間與永恆的延續,則是歷史的意義。本文是根據《天主之城》,探討奧斯定的歷史觀。首先是有關天城與地城的思想淵源,其次是本書的性質,最後是奧斯定的歷史觀。
- 期刊
我們應該靜態地看待證據,還是應該動態地考察證據與探究的過程?對於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構成了證據主義與德性知識論的根本分歧。證據主義堅持一種狹隘的證成觀,主張認知證成只涉及證據與信念的關係,與探究行為無關;德性知識論則遵循自然化知識論的思路考察信念的病原學,主張證據與探究應該獨立共存,並基於理智德性重塑信念證成(個人證成)與命題證成的關係,拓展了認知證成的本質內涵。總之,德性知識論成功地調和了傳統知識論與自然化知識論之間愈發尖銳衝突和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