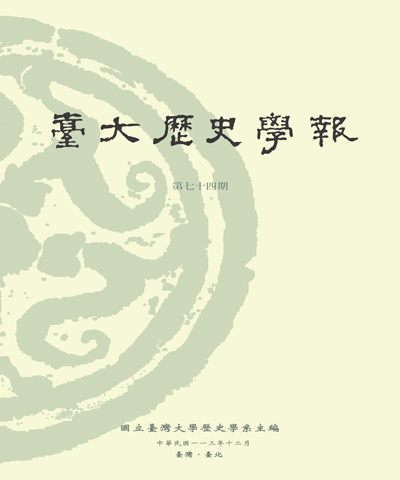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臺北帝國大學(臺北帝大)於1928年設立,其後身國立臺灣大學(臺大)於今年(2018)舉辦90週年校慶活動。學校建校歷史推算至日本時代,是解嚴後的趨勢。然而,1945年的大變局影響臺灣至鉅,學校縱使有前後身之關係,其間斷裂恐多於承繼。本文選取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學」作為研究對象,試圖重建該專攻(含同名講座)的歷史,及其戰後演變。本文首先敘述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的經過,並探討名稱由「臺灣帝國大學」變更為「臺北帝國大學」的原因。臺北帝大的創設宗旨,以臺灣.東洋.南洋之自然界及人文界為研究對象。這是以地理位置定義學術方向,也因此文政學部史學科有別於其他帝國大學,設有「南洋史學」之講座與專攻。透過資料整理,本文嘗試勾畫南洋史學的講座、編制、專攻,以及課程。誰來讀南洋史學?以臺大校史檔案為根據,本文提出較為完整的圖景,尤其是鮮為人知的戰爭期景況。南洋史專攻的學生中,以中村孝志(1910-1994)與張美惠(1924-2008)最有關係,因此特詳予描述。張美惠「具體」過渡到戰後的臺大,另外受日本史學訓練、研究越南史的陳荊和(1917-1995)也加入教學陣容。張、陳二人延續臺北帝大的南洋史學傳統,惟因種種原因,二人相繼離開臺大。此後,臺大的南洋史研究中斷26年,最後由曹永和(1920-2014)賡續臺北帝大的南洋史研究。
- 期刊
臺灣在戰後初期去殖民化的時代背景中,有關日治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延續,目前主要以制度史與政策研究為主,然而不同學術領域具體內容的繼受與轉型,以及個別行動者的角色,有待進一步考察。戰後初期,官方對日治時期殖民地的學術成果,採取「知識的接收」政策,日本考古學者國分直一(1908-2005)在戰後留用4年期間,整理臺灣考古學與民族學的文獻及標本資料,且透過在臺灣大學史學系的教學與田野工作,培育並影響了戰後臺籍第一代的人類學家。本文分析國分直一在戰後臺灣歷史轉型過程中,在整理臺灣研究學術成果與教育扮演承先啟後的角色,以及戰後初期臺灣史前文化的解釋模式,從多源到單源的轉變。
- 期刊
什麼是科學革命?科學知識社會學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分別提出貌似不可共量的解答。有鑒於此,本文試圖以「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the first Darwinian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為例,自拼裝觀(assemblage thinking)汲取靈感,回應此問題。所謂「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係指哈佛大學植物學者格雷(Asa Gray, 1810-1888)與其同事阿格西(Louis Agassiz, 1807-1873)於1859年就物種起源及分布展開的爭議。即便該爭議已被廣泛討論,然研究者至今仍未回答:為何該爭議涉及「北太平洋探險」的調查成果?何以日本植物相成為兩人爭議的焦點?格雷為什麼會對日本植物相感興趣?他如何自日本及其周邊區域取得研究材料?受拼裝觀的啟發,筆者不以社會利益/興趣解釋兩人爭論的根源,也不分析他們如何將自身建構為不可取代的「計算中心」。本文強調,拼裝觀主張社會現實及其變遷均涉及人與非人元素跨尺度的隨機與偶然連結,似更能幫助研究者摒除「社會」與「自然」等既定範疇,壓低姿態,細索這些範疇如何浮現與穩固。拼裝觀於認識論與本體論的立場,或可在兩種面向上幫助理解「什麼是科學革命」:第一,將格雷、阿格西與達爾文等學術名人去中心化-除了關切人蔘、大鯢、毒漆樹等物件於其思想脈絡中的位置,更讓植物採集者、在日本等異鄉以武力協助採集者的指揮官等「隱形技師」現身;其次,以全球視野審視演化思想史上的變與不變,又不至落入全球與在地、西方與東方等二元對立的窠臼。
- 期刊
相較於社會經濟史研究,歷史學者對中國經濟思想的關注明顯不足。現有的中國經濟思想史著述,多由受經濟學訓練者撰作,主要利用經濟學的理論和術語,歸納、分析文本與思想家關於經濟行為的觀點,再從現代的眼光予以評價。這種作法往往難以避免時代錯置和理論先行的缺憾。具體至春秋時期的經濟思想,既有著述的不足尤其明顯。本文將重心放回文本,以論述的思想史取徑,透過《左傳》、《國語》說明春秋時期經濟觀念的性質及其表現方式。本文指出,「禮」是《左傳》和《國語》經濟論述的核心關懷,或隱或顯地見於諸般討論,包括資源生產與開發、環繞生計所見的政治社會理想、匱乏與資源分配問題,和個人層次的經濟追求等。在「禮」的構想下,《左傳》、《國語》經濟論述的內涵,是強調生計所需和資源、社會上的互惠關係。本文也嘗試透過其他材料,說明《左傳》、《國語》經濟論述對其後思想家和文獻的可能影響。要言之,經濟論述是古代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面向,歷史學者應盡可能減少各種現代概念的包袱,從文本及時空環境出發,探索、重建古人何以且如何考慮財富與物質資源。
- 期刊
Traffic between Jakarta (and later Batavia) and Nagasaki was unusual before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established its trade to the two destinations. In the mid-17th century, Chinese junk traders under Zheng Chenggong's (鄭成功) protection ran this business from Amoy. After the 1650s, the commercial strife between the Zheng clan and the VOC threw a spanner in the works that eventually resulted in a war in 1661. In 1669, the Batavian authorities gradually relaxed their control over the Chinese junk trade on the Nagasaki-Batavia route. The antagonism between the Zheng regime in Taiwan and the VOC in Batavia, compounded by that between the Zheng and the Qing court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reated a loophole for the Batavian Chinese to run the business on the Nagasaki-Batavia route in 1665-1719. This article has consulted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archival sources to clarif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usiness of the Batavian Chinese on this route and also the duration of this voyage, the numbers of the crews, and the carried cargoes.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blind eye turned by the Batavian authorities was crucial, and this trade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plantations owned by Batavian Chinese officers. Their experience in exploiting the leeway granted by different states was the legacy that l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later junk traders on China Seas in the 18th century.
- 期刊
臺灣史學界對於劉銘傳(1836-1896)等人自強新政(1886-1891)中財政改革的分析,主流觀點認為其改革的確大量增加了臺灣的歲入,並達成一定程度的財政自主化與理性化。但這些分析缺乏制度面向的歷史考察,也未定義所謂的理性化,因此難以適當定位晚清臺灣財政改革的歷史性質。本文利用晚清臺灣各種史料,依序分析劉銘傳新政時期在田賦、鹽政、釐金與關稅等徵收體制上的改變,並統計改革前後田賦、鹽課、釐金與關稅數額的變化。經由這些定性與定量分析,筆者發現劉銘傳的財政改革雖在某些層面上改變臺灣的稅收體制,增加不少收入,但並未改變家產官僚制的傳統徵收方式。因此,晚清臺灣的財政改革,僅是傳統帝國財政體制框架內的一種內在調整,不具有近代理性化意義。
- 期刊
清康熙五十年(1711),臺灣巡道陳璸(1656-1718)擇臺灣府邑郊永康里之地,初建萬壽亭,作為三大節的祝釐場所,今已不存。近年相關文籍或因古志記載萬壽亭南向且其前有德慶溪流經之說,遂界定德慶溪源北濱、現國立成功大學勝利校區一帶即該亭肇建地點。本文比對查考多幅清代輿圖,檢視梳理文書記載內容,歸納得出舊萬壽亭基址點位座落小東門、開元寺和大北門間的三角形地區內,近乎介於臺灣鎮標中營營盤和開元寺兩地一線之間,距離開元寺約莫當時的1里至2里路程,而鎮標中營營盤係在今成功大學光復校區。據此,本文重新推定萬壽亭舊址應在北區仁愛里西境之東豐路一帶,南距德慶溪源頭約1公里。此一推定範圍並得以由其空間使用的變遷脈絡、歷史環境的地理關連與位置敘寫的重新解讀等面向,獲得論證支持。萬壽亭選址除了可能反映地質環境條件的考量外,作為皇權象徵,使之得以與旁鄰高級軍事區相互生產臺島最高治權核心場域的空間意義,且因地界在府城中路防務上的戰略重要性,亦能和前述軍事區發生緊密連結,其區位意涵聯繫了清代郡治中自崁頂山至城西、從馬房山到德慶溪間之權力意象和軍事功能地景,此有助於理解並形塑今日當地文化資產空間的歷史脈絡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