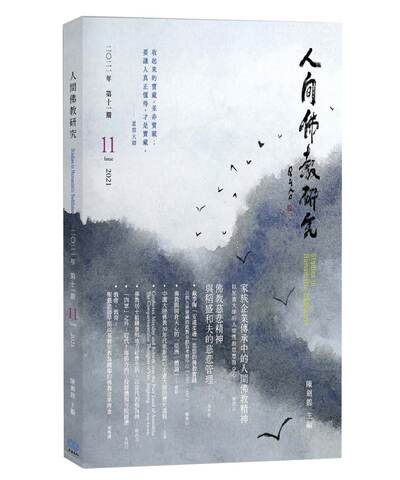
人間佛教研究/Studi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星雲大師一生強調「同體共生」的思想觀念,希望大眾和平共處,共獲幸福人生,進而在種種福報的基礎上,修持慧業。大師定義「同體」的意涵為「平等、包容」;定義「共生」的意涵為「慈悲、融和」。他總括地指出:「『同體』是平等觀,『共生』是慈悲觀。」大師說:「沒有了慈悲,所行的一切都是魔法。」這即是《華嚴經》所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為魔業。」可見,大師依此建構他的「共生慈悲」的理念,於理有據。日本學者鎌田茂雄教授認為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思想建基於《華嚴經》;大師自己亦曾說當初建設佛光山,所設計的「華藏世界」是根據《華嚴經》中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的理念構想而成;此亦可視為大師有依華嚴思想來建構他的「同體共生」的理念。本文最後反省以共生精神,來建立人間淨土的問題,指出建立淨土雖不容易,但給予眾生信心、歡喜、希望、方便,令其有目標可循,何嘗不是從小幸福趨向大幸福,乃至極幸福之境的方便施設。大師倡導人間佛教,其終極關懷在於建立人間淨土,如果人間就是淨土,那麼,西方極樂世界就在人間,表示「共生」的「淨土」得以在人間成就、完成。
- 期刊
星雲大師多年來推動「人間佛教」,期許建設「人間淨土」,發願生生世世到人間行大乘菩薩道,化度大眾修學佛法。事實上,根據星雲大師早期在各地弘法演講、佛七法會開示等文獻來看,屢有提及推崇阿彌陀佛西方極樂淨土之言論。星雲大師「建設人間淨土」的願心雖與傳統「求生極樂淨土」的思想有所區隔,實際上並未反對傳統的極樂淨土思想與持念阿彌陀佛聖號之法門。星雲大師坦言在念佛實修中受益良多,因此本文旨在探究星雲大師早期弘揚彌陀淨土的芳躅及其對念佛法門的詮釋。星雲大師宣揚念佛功德,不僅依據古德詮釋傳統,亦善用現代化概念來彰顯念佛法門之殊勝。為將佛法修持落實於生活,星雲大師認為現代人適合「持名念佛」,此法不受身份、時空之限制,大眾透過念佛得以淨化身、語、意三業,消除現世諸苦難,彰顯念佛法門的積極意義。對於念佛所應掌握之心境,星雲大師從實修中汲取出「歡歡喜喜」、「悲悲切切」、「空空虛虛」、「實實在在」之精要,勸勉大眾仰仗持念阿彌陀佛之「正念」來對治「妄念」,更須從持念彌陀之「有念」進入破除我執之「無念」,自能與阿彌陀佛感應道交。
- 期刊
星雲大師主張以文教弘揚人間佛教思想,他創作的大量文學作品,流傳海內外,受眾面廣,影響力大。這些作品是星雲大師創作活動的成果,也是他思想的重要載體。對星雲大師的文學創作觀進行研究有助於我們對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思想及佛教文學的發展有更好的瞭解。我們嘗試選取從中國古代文論的三對範疇,從它們入手對星雲大師對於文學創作的一些基本觀念進行探討。情和志討論的是文章的發生是出於抒發個人情感還是關懷社會家國的問題,星雲大師主張情志交融,二者有相互溝通的地方,可以互相促進。言和意涉及語言本身和其表達的意思的關係,星雲大師看重語言的表達能力,但也認為語言有局限性,有一些比較高深的內容是不能表達出來的。文和質實際上是文章的形式和內容的關係,星雲大師對「質」的重要性更為強調,但也注意到文章形式、修辭這些文學性的一面,認為文章的形式是為內容服務的。
- 期刊
本文以星雲大師《星雲說偈》二冊著作為主要探討文本。首先,析釐星雲大師如何消解禪宗「不立文字」與「文字般若」間的矛盾,引出大師一生筆耕不輟,視筆如拂塵,欲掃去人心之障垢,更冀望透過文藝創作來弘揚佛法,落實「佛法文學化」、「以文化弘揚佛法」的理念;進而闡述《星雲說偈》的文學性。次之,從大師對《星雲說偈》詩偈的詮釋,爬梳其人間佛教思想的意涵。
- 期刊
本文將作跨領域的探討,目的是將佛教及中醫對於人心的關懷就調心方法方面作一比較研究,並探討星雲大師對於心的觀點和調心方法。本論文屬於文獻分析法,透過佛教與中醫調心方面之文獻作分析比較。佛教是一種信仰,中醫是一種醫學。佛學是自力的淨心,中醫是他力的治療。二者有異同之處。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需要走入人間,可由佛教最重視的「心來著手」。二者的比較研究開啟了整合的可能性。
- 期刊
在近現代的人間佛教發展中,「佛教心理學」一門學問日漸發展。佛教與心理學之結合其實已有一段不淺的歷史。就華語學界而言,早於清末民初的年代,太虛大師已曾就〈佛教心理學之研究〉一題作出演講;梁啟超亦為心理學會作演講,題目為〈佛教心理學淺測〉。時至今日,佛教心理學的發展未曾止步。就專業的層面而言,在學術界的發展中,佛教心理學已儼如一專門性的學問範疇。就大眾的層面而言,針對都市的高壓力、情緒病日益嚴重、都市人不懂放鬆等問題,坊間上已有不少佛教心理學的普及性讀物。可見,佛教心理學的影響力日漸提升。不論是對學術界乃至大眾社會而言,它都有著不可忽視之價值。佛教心理學的影響力和學科成就雖然與日俱增,可是展望其未來發展並非全無隱憂。佛教心理學至今仍未見系統性回顧學科發展之論述,學科發展的現況、成就與有待改善之處亟待研究和反思。有鑒於此,本文盼能為學界填補此一空白處。本文旨在反思佛教心理學的學科發展,並重新省察佛教心理學如何能與社會科學之精神作有機結合,令這門學問於未來得以充份發揮所長。經過檢視學科的現況後,本文建議設立符合人間佛教藍圖的「應用佛教心理學」,令社會大眾更能受益於這門學問的好處。
- 期刊
1948年10月,慈航法師(1893-1954)應中壢圓光寺妙果和尚(1884-1963)之邀,從新加坡來臺主持「臺灣佛學院」,僅半年而解散。1949年國共內戰國府失利,同年5月20日臺灣全島戒嚴,開始肅清島內共產黨潛伏勢力,大陸來臺人員首當其衝。1949年6月,因「匪諜事件」與一群大陸來臺學僧繫獄月餘。出獄後直至同年底之前,仍是風聲鶴唳,居無定所,直到靜修禪院玄光(1903-1997)、達心(1898-1956)二師允建彌勒內院後,慈航法師方得逐漸安頓。大約在1950年春,因洗刷疑似「匪諜」嫌疑,各界緇素競相邀請弘法。1950年8月,彌勒內院落成之前,慈師曾應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長宋修振(1911-?)之邀,作一環島演講。彌勒內院落成後一年,1951年9月,受政府委託,與甘珠爾瓦(1914-1978)一行六人,下鄉宣傳反共抗俄國策,並宣揚佛法。在1952年9月閉關彌勒內院之前,這兩場大規模的弘法具有相當性的指標意義。1950年6月,韓戰爆發,最終在1953年7月兩韓簽署停戰協議,為防止共產主義輸出,1954年12月初,國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韓戰轉移了中共犯臺的注意力,而「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則保持了臺海和平數十年。本文旨在探討慈航法師主持「臺灣佛學院」解散後所遭遇的「白色恐怖」,以及汐止彌勒內院落成前後,1950年夏與1951年秋的兩場環島的布教活動。
- 期刊
本文主要從湛然的《十不二門》和《金剛錍》,探討其「無情有性」論中的「色心不二」觀。基本上,湛然談佛性與法性的互融、有情與無情的相即,就是從上述一念心具三千諸法的天台家要義為依歸的,而此義所要闡明的,扼要來說,乃是一念心與世間萬法,如何藉着兩者二而不二、不二而二的互動歷程所構成的世界整體。職是之故,湛然談佛性法性的相融、有情無情相即的理論根據,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心物(色)互相涵具的相依性,因此,若要證成「無情有性」,就不得不涉及心物的不二體性與內在聯繫等問題。此所以在湛然的「無情有性」論,不難發現談及色、心關係的言論,在《十不二門》裏,更以「色心不二」為首門,作為其餘九門的所依,這都顯示在湛然的學說構造裏,「色心不二」觀實佔有舉足輕重的位置。湛然透過色心、諸法的互涵互具,展示一幅在一念中三千世間交相融通的全景式圖像。在宗教實踐的意義上,乃在令人向「三千統攝於一念,一念間三千互具」的世界觀回歸與靠攏,以便在人的內心深處,形成縱深廣闊的精神結構,在一念間的任何一個切入點,都可讓心識力量,縱橫盡得,隨時切入凡聖一如,心物相即的精神場域,透達三諦圓融的不思議止觀之境。
- 期刊
漢譯《華嚴經》共有三種:六十《華嚴》(佛陀跋陀羅譯)、八十《華嚴》(實叉難陀譯)、四十《華嚴》(般若三藏譯)。從東晉安帝義熙十四年三月(西元418年)始譯《六十華嚴》。到唐代時,隨著《八十華嚴》和《四十華嚴》的傳入,中國達到了《華嚴經》的翻譯、研究、傳播和接受的頂峰,三種《華嚴》的翻譯與研究跨越380年。文章試圖以《華嚴經》的文獻研究為依據,將思考的重點集中在三種《華嚴》的文本構成與文獻考辯上。此外,文章也注意到了近百年來學術界對《華嚴經》的研究,從六個方面描述了百年華嚴研究的新氣象及其不足所在,力圖完整勾勒華嚴研究的百年全景,為學人提供基本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