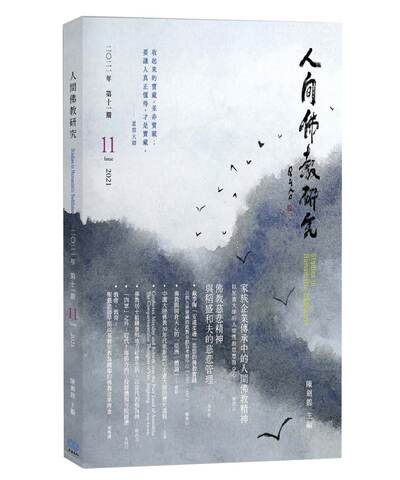
人間佛教研究/Studies in Humanistic Buddhism
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本文設定有限的論述目的,具體的說,本文先分析佛教的慈悲觀的理論成分,從哲理分析,提出從存在論、形上學及本性論三向,解釋生緣、法緣與無緣慈悲的三層次;並凸顯慈悲的四個面向,它們分別是意向性的關聯、位格的關係性、平等的同理性及動態的實踐性;並進而以日本京瓷創辦人稻盛和夫為例,以彰顯在其詮釋下,所見到的佛教慈悲精神跟慈悲管理的選擇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
- 期刊
家族企業的傳承困境,已經成為華人甚至全球家族企業的重要問題。佛教組織和家族企業,都面臨著長久傳承和現代化的問題。佛光山提倡和踐行人間佛教精神和佛教現代化的成功,星雲大師的圓融智慧是值得家族企業處理接班問題借鑒的。本文在分析了從佛法角度研究家族企業傳承的可能與必要性之後,結合歷史案例,從要持戒、要禪定、要放下、要專注、要發心等方面,論述了人間佛教的禪心法門對家族企業的成功傳承可能的啟發和作用,以期望人間佛教的甘露能夠幫助家族企業更好的完成代際更替。
- 期刊
國民政府的重要高官戴季陶,實為國家元首蔣中正處置邊疆事務及佛教事務的最重要智囊。他與身處內地的九世班禪有著深入的公私往來。從政府層面講,九世班禪發自內心以佛教領袖身份竭誠為國分憂;從私人層面講,雙方結為金蘭法侶僅僅數年,情誼即急劇升溫。這種為穩固邊疆的運作最終奠基於一樁樁鮮活生動的具體實務中,促使蒙藏民族開啟傾心內向的新旅程。1930年代的戴季陶,在與藏傳佛教領袖九世班禪的友誼之路中採用「敬一人,千萬人悅」的近代中國穩藏思路值得思考。
- 期刊
岡倉天心(Okakura Tenshin, 1862-1913),原名岡倉覺三(Okakura Kakuzō),是近代日本民族啓蒙運動時期的核心思想家之一,在就讀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期間,成為時任東大哲學教授的東方學家費諾羅薩的學生與助手,在其影響下,與之一道致力於拯救東方藝術和日本文化。岡倉天心分別於1893年、1906年、1908年和1912年四次到訪中國,為波士頓美術館東方美術部收購大量中國珍貴古畫與佛教藝術品;1903年至1906年間,岡倉天心出版了包括《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1903)和《茶之書》(The Book of Tea, 1906)在內的四本英文著作,在西方產生極大影響。基於對岡倉的生平與著作之梳理,筆者發現他在宣揚與維護東方傳統美學理想和呼籲西方對「東洋」的關注時,一再借助中國古典藝術和佛教思想傳達其強烈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一體論」,其思想透露出矛盾性與前軍國主義思想。基於此,本文將從親歷中國、書寫東方、展示東方三個層面展開分析,探討特殊時期佛教思想和藝術對岡倉天心的重要影響,總結岡倉天心的跨文化想像心理機制,以及他在近代中國時期借助佛教所建構起的全新的日本現代民族闡釋模式。
- 期刊
太虛大師是現代佛教革新運動的一代宗師,他提出的人間佛教思想,被海峽兩岸佛教界所繼承和實踐。如今,中國大陸漢傳佛教推崇太虛大師、建設人間佛教,已成為一個鮮明的時代特點。然而,在50年代中期開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由於政治形勢敏感性,大陸佛教即使是太虛大師門下,也長期不敢公開提及「太虛」之名。80年代,大陸佛教界及學術界重新認和學習太虛大師的進程中,趙樸初所起到的作用是無人可及的,促成了大陸佛教回到太虛大師人間佛教的道路。他以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政協副主席等政治威望,通過官方和私人兩種途徑,尤其是與太虛大師臨終前一段交往的「敘事」,推動並且擴大了太虛大師及人間佛教思想在大陸僧尼信眾中的影響,成功地將人間佛教確立為中國佛教發展的主流方向。
- 期刊
Amitābha (nianfo 念佛), but also a this-worldly focused moral Confucian cultiv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Ven. Jingkong's online dharma talks and publications, the present article identifies the Confucian notion of filial piety (xiao 孝), and one specific paragraph of the 'Sūtra of the Meditation on the Buddha of Immeasurable Life' (foshuo guan wuliangshou jing 《佛說觀無量壽經》)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is advocated soteriology. This Sūtra provides the Buddhist textual foundation of xiao, thus erecting a bridge to connect the Sūtra with Confucian and Daoist texts, such as 'The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xiaojing 《孝經》), 'Rules for Disciples' (dizigui《弟子規》), and 'Treatise of the Most High on Action and Retribution' (taishang ganyingpian《太上感應篇》),' ipso facto explaining the incorporation as well as the 'Buddhicising' of the former texts. In this sense he emphasise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one's fate - and therefore the chance to be reborn into the Pure Land - is not the result of acts of worship towards Buddha or the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of rituals or even the renunciation of all worldly distractions, thus 'going forth' (chujia 出家) and entering a monastic environment, it is rather based on 'correct' moral conduct in daily life, through acts of filial piety, compassion, honesty, and humility - which are de facto Confucian values. This train of thought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 'compartmentalism' because Jingkong argues that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address different domains of reality and truth,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ddress specific issues without interference. Thus, they constitute a parallel space within their shared universe of discourse: Buddhism gives reason to what holds the world together at its core and being focused on extramundane salvation, whereas (selected parts of) Confucianism explain how to conduct oneself in the world. These selected parts are then re-interpreted through a Buddhist lens and integrated. Thus, not triggering any conflicts regarding their soteriology, that needs to be reconciled. The article, therefore, investigates the questions: how does a Pure Land advocate rationalises the incorporation of other tradition's morality concepts through certain narratives, what termi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describe this phenomenon, and finally, why does Jingkong emphasise this-worldly cultivation based mostly on the 'Rules for Disciples'?
- 期刊
中國居士佛教及其組織實踐歷史悠久,幾經變遷,始終是佛教的重要社會基礎和影響力量。基於宗教性志願原則結合起來的居士組織,起著聯合佛教與社會的重要作用。當代中國西樵鎮的佛教居士組織,組建形式多樣、人員構成多元、活動内容豐富。不僅在微觀上幫助西樵民眾形塑多彩的日常生活,滿足人們各種需求;宏觀上也推動多元社會共同體和公共空間的形成,有利於民間組織和地方公益的發展,無疑是現代社會建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佛教居士組織之所以能積極有效地參與地方社會生活,根本原因在於以佛教信仰為背景的宗教性志願力產生出源源不斷的集體意志和社會行動力。此外,西樵個案存在的問題表明,居士組織的健康發展也離不開中國佛教和中國社會自身的建設完善。
- 期刊
本文關注近代中國佛寺中的工役,通過這一特殊群體探討百年來都市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和變遷。寺工群體歷來數量龐大,是叢林生活中的必要組成部分。近代以來,都市佛寺興起,提供服務的寺工在寺院經濟中的作用愈發重要。然而,在這種佛教服務業的僱傭關係下,寺工們的宗教身份也變得模糊起來。在二十世紀40、50年代,圍繞著勞資糾紛與僧俗矛盾的雙重衝突,寺工們開始組建工會以求抗爭佛教會。隨著時代的迅速變化,雙方的境遇也幾度逆轉。本文依據報刊、檔案、調查報告和回憶錄等資料,著重考察上世紀40、50年代上海地區的寺僧與工役的糾紛事件,還原雙方的博弈過程及其背後的觀念。透過寺院工役群體近百年來的命運變遷,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近代寺院的運作方式,並從新的角度發掘「都市佛教」寺院經濟的特性。
- 期刊
本文所嘗試探討的是聖嚴法師(1930-2009)於主要在1950年代後半針對台灣佛教現況所提出的改革建言,及當中與基督宗教組織事業、傳教形式相契合之部分。取材為其從軍來台後,尚未重新出家前以「醒世將軍」等為筆名所發表於佛教期刊中的文章,尤聚焦〈站起來吧,中國佛教!〉(1957)、〈敬為中國佛教的現狀請命〉(1958)、〈一個問題兩點意見〉(1958)三篇。所提供觀察包括:彼等論述一定程度上與民國時期新僧們所發表的類似,但同時考察聖嚴個人生涯事業,及同時代佛教發展的走向趨勢,會發覺這些即使是早期的言論卻和往後行動相互呼應。此乃基於中國佛教來到海外台灣、香港等地,其發展環境已能逐漸允許更多改變和創新。另一方面,本文回顧大陸近現代佛教改革及向基督宗教借鑑的歷史與研究成果。同時敘述了中國佛教於1949年國共分治後轉移到港台的情況,和50、60年代兩地所發生的佛耶辯論。以作為聖嚴發言的相關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