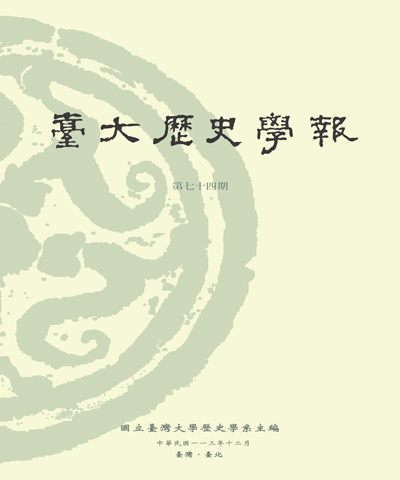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武舉和武學在宋代的制度化,是文士將讀書和科考的理念應用於武官選任制度的結果。倡議者期待透過學校教育與考試制度,選拔「知書之將」,以改善武官的素質。但是,以書本教育與紙筆考試選拔將才的結果,卻與設立的宗旨大異其趣。參與者大多數是受挫於文科考試的士人,他們對於軍事工作並無興趣,只是以武舉和武學作為求取官職的另一途徑。因此,武舉進士多半不願加入軍隊,只想尋找改換文階的機會。從北宋到南宋,武舉進士不願從軍的現象日益嚴重,就軍事層面而言,武舉的功能是隨著時間而遞減。 儘管在軍事層面上的效果有限,武舉與武學仍然持續運作直到南宋滅亡。這是因為這兩個制度兼具象徵意義與現實功能。武舉和武學代表政府對於「武」的重視,使宋朝具備「文武兼隆」的外貌,並可確立讀書有益於統兵的觀念,合理化文官對軍隊的掌控。在現實層面上,武舉為受挫於文舉的士人提供出路,減少科舉競爭的壓力,由於牽涉到眾多讀書人的利益,政府儘管對武舉的成效感到不滿,卻難以將其廢除。 武舉與武學的名不符實,顯現軍事知識在宋代尷尬的地位。文士提倡軍事之學,卻不肯承認「武」自有其學術體系和價值觀念,只想以「文」的理念來應付「武」的問題,致使「武」成為「文」的附庸,限制了整個國家在軍事頜域的發展空間。
- 期刊
本文仔細分析了朱子視經典為「聖人之書」,讀經典是為了學聖人並認識恆常的天理這兩個概念;並將朱子的思路與當代的存有詮釋學做一比較,指出兩者間的一些基本差異。對於朱子而言,經典的核心價值,在於它們是聖人之書;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則在於他們徹底體現了大公無私的天理。在朱子看來,讀者有可能瞭解經典的「本意」,其原因在於作者與讀者分享了共同的宇宙與人生道理。相較於存有詮釋學從此有出發,強調人類知識與理解不可避免的有限性與主觀性,朱子則一方面強調人的有限性,一方面卻提出大公無私的聖人境界,以為道理與做人的極則。他認為聖人從一種無執無我,亦即無私的心境所自然流出或照見的道理,極其深刻、平實、精密、普遍、周延,而能夠成為人們所共同分享與認知的最高道理。這種以心性修養為基礎的聖人之學,並不在存有詮釋學的視域之中。二者的基本差異,應在於對無我之境與有我之境的看法。朱子以無我之境界為最高的追求,所以更重視那具有「恆常性」意義的天理人性;而存有詮釋學則特別強調並探討人類存有與知見的主觀性及限制性。
- 期刊
自隋唐時期開始,科舉便是國家選拔官僚的重要制度,宋代君主對進士科的重視,更使得進士出身的官員在政治上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契丹遼朝與早期的金朝君主也用科舉選取官員,但是這些官員的地位和影響力,往往不及契丹、女真的功臣子弟或宗室貴族。而進士考試似也從未成為統治族群入仕的管道。直到金世宗(1161~1189在位)大定十三年(1173),配合世宗的譯經事業,首次舉行以女真字學學生為對象,用女真文字考試的女真策論進士科考試。由於這一次考試的成功,大定二十年(1180)之後,女真策論進士正式成為金代科舉的項目,一直到金末。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在於釐清這個制度成立的過程,暸解世宗及其他女真臣僚為何試圖透過這個政策,達到提升女真子弟之文治能力的目標;第二,在於從女真進士政治上的表現,分析經由這個管道入仕的女真文治人才,對於女真政權內部的權力分配有何影響。
- 期刊
方豪神父(1910~1980)以其學者與教士的雙重身分,在民國天主教史上有不同於一般神父的特殊地位。 他以大學教授的身分,從事傳教工作,向知識階層的傳教自然成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環。一九三八至四一年主編《益世報》,一九四六至四八年主持上智編譯館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年從事臺大天主教同學會之輔導工作,均為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同時,他以言論宣揚公教中國化之功,更為其畢生職志所在。本文主旨即在闡明他在這方面對天主教會的貢獻。此外,對他與天主教領袖田耕莘樞機主教、于斌樞機主教及徐誠斌主教間的關係,亦有所探討。
- 期刊
過去日治時期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大多忽略殖民地的區域性差異和不平衡發展問題。本文則透過東臺灣地區會社的發展軌跡和企業家的特性,指出東部產業發展在整體殖民地經濟史的位置和特色,以及在臺日資在殖民地邊區的特殊地位和角色。 東臺灣地區直至日治時期仍是一個低度發展的地區,其會社的類型、產業類別以及資本規模的發展模式,均與全臺不太一致,充分展現其位居殖民地邊區的獨特性。東部會社的發展,以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為限,經歷了兩個階段的變遷。一是一九三○年代以前,東臺灣的企業主要由明治至大正年間先後來東臺灣的在地日本企業家所主導。西臺灣常見的日本國內大財閥,則由於東產業開發條件之限制,顯然較缺乏投資的意願。二是中日戰爭的爆發,顯然為落後的東臺灣帶來發展的新契機。為因應戰時資源開發的需求以及東部交通建設和理番成效之顯著,在國家和企業的協力之下,東臺灣進入產業的勃興期。日本國內財閥於此際積極經營東臺灣,甚至於連日本國內數一數二的重要新興軍需重化工業均在此時進入東部。東臺灣的花蓮港廳,一反過去殖民地產業開發邊區的位置,成為當時新興重工業的重鎮。臺東和花蓮港廳產業的異途發展,乃從此展開。
- 期刊
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崛起於一九○○年代,民國成立之後並蔚為新文化及五四時期激進思潮的一脈主流勢力。本文的主旨即在於闡明無政府主義作為一種近代激進主義的結構性特質,並在現代情境的兩個基本面向的脈絡下,探討其崛起的原因、意涵及意義。本文的主要論旨是: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雖奠基於一種有關「自然秩序」的原始主義式信念之上―亦即:相信在國家的組識興起之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一個人人自由、平等、獨立而社會和諧的「原人」時代―但它乃是道地的現代情境下的歷史產物;它既是對傳統社會政治秩序解體的回應,也是對近代西方資本工業文明之擴張的回應。本文認為,無政府主義所回應的這兩方面的問題,相當關鍵地界定了中國所遭逢的現代情境的基本樣態一唯其如此,無政府主義遂得以吸引大批的信徒,同時也藉由它對社會革命理念、理想的持續論述,而為日後共產主義的興起發揮了積極助援的作用。然而由於近代西方資本工業文明之擴張,乃是以帝國主義軍政勢力入侵的形式對中國造成威脅,因此營建國族的民族主義政治目標,自始即是內蘊於此一情境的一個重大問題環節,但無政府主義者對之卻是無力回應的。此一無力回應的事實,不僅使得無政府主義漸失言論市場上的競逐力,同時它所導致無政府主義者的虛空、焦慮之感,亦為共產主義的興起發揮了一定的消極助援作用。
- 期刊
本文論稱,古典無政府主義者,例如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1836)、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巴枯寧(Michael Bakunin, 1814~1876)和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1842~1921)四人,在創建一個可能的自由社會的論述上,共持相同承擔。然而,這四人的思想,分別代表著四種不同的流派: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互助主義(mutualism)、集產主義(collectivism)和共產主義(communism);斯四子對此承擔,自有異同的論述。此外,本文亦將揭露出,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兩方在理論上關鍵性的差別。最後,本文嘗試對無政府主義社會的願景的限制與可能,給予一評估。作者相信,無政府主義並非是一種荒誕狂想,與現代政治思想及生活無涉無關;相反地,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思想概念,其特性與所長在其具有超越當下環境的限制的力量、在開啟另類思維的能力,以及在為政治行動重覓新路的衝動。總之,拙文試圖提出一種概括性的觀點來析論現代無政府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