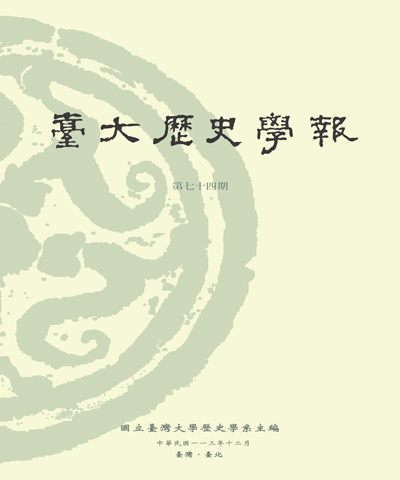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本文討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與中、日、韓各國政治權力的複雜關係。本文除運用東亞儒者註解《諭語》與《孟子》等經典的資料之外,也使用明代科舉考試試題,與德川時代日本宮廷講官進講《孟子》時所批註之「御讀禁忌」資料,以及中國漢代與唐代君臣對話中所引用的經典資料。 本文指出: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者身兼儒者與官員之雙重身分,所以他們的經典詮釋事業與政治權力開係密切。約言之,兩者之關係有三:第一,經典解釋與政治權力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兩者之間有其競爭性;第三,詮釋者致力在兩者之間維持平衡性。 總而言之,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者實透過他們所處的「存在結構」(existential structure)而理解經典,也賦于經典以「實存的」(existential)內涵。
- 期刊
漢代以後的政府深受儒家政治理論的影響,堯舜和三代是儒者最常提及的治國典範。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深為後代統治者所欣羨,而其事蹟記載詳盡,易於仿效,在中唐以後有另成典範之勢。進入五代十國時期,期待唐太宗復現的意見仍然常見,至北宋建立後,循貞觀之政以復三代之治仍是常見的政治主張。但是,從仁宗朝開始,隨著儒學的開展,部分文士開始批判唐太宗,提倡恢復堯舜三代之制以超越漢、唐。他們希望藉著政治的改革以達到重建禮樂與移風易俗的目的。 但是,當王安石、蔡京高舉「三代之法」以合理化自已的施政,反對者一方面質疑他們的具體作為不符三代的理想,一方面援引貞觀之政為典範加以對抗。堯舜三代與貞觀故事道在部分政治論述中被描述成不同的典範。宋室南渡後,唐太宗的典範因與恢復中原的理想相吻合,再度受到統治階層的重視,而朱熹等理學家則再度嘗試重建三代的文化秩序。朱子將貞觀君臣的作為定位為以「求利」為目的,與「堯舜三代」根本不能相合,乃引發了陳亮的批判,形成了二人間的王、霸之辯。 南宋末年,程朱之學成為學術上的「正統」,文臣諭政多半提倡堯舜三代而貶抑貞觀之政,但對統治者而言,「堯舜三代」邈遠而模糊,遠不如唐太宗「一統華夷」的成就來得有吸引力。從中唐至南宋末,不諭儒臣對貞觀之政的評價如何改變,多數君主們對唐太宗典範的嚮往卻始終未衰。這是在分析宋神宗與王安石,孝宗、理宗與南宋理學家於施政理念的矛盾時,可以思考的角度。
- 期刊
明代羅旁瑤區,地處廣東西江南岸,控扼著作為兩廣交通咽喉的西江水道。明朝開國後,此地瑤亂頻仍、剿撫不定的局面持續了兩百年之久,直到萬曆四年(1576)經過軍事大征後,才被真正納入王朝統治體系。 本文依據相關原始文獻,重點考察李材在萬曆初年嶺西兵巡道僉事任上,圍繞當時盛行於士大夫之間的講學活動以及大征羅旁計畫的提出和實施,與首輔張居正、兩廣總督殷正茂之間的複雜政治糾葛。而大征最終能夠取得決定性成功的關鍵,不僅在於熟悉地方社會事務的任事官員提出詳細周延的作戰計畫,同樣重要的是,張居正執政時期,朝廷和地方政府在處理社會事務上的密切協調與合作機制。
- 期刊
臺灣在明朝不是中國的領土,雖然距離沿海信地澎湖很近,但明朝人對臺灣的認識很不切合實際。這篇論文昌在探討明人的臺灣認識的情況,以及此一認識由粗淺的印象到具體接觸的演變過程。 正文分為五節。首先討論有關中文文獻之「夷洲」與「流求」的長年論爭,特別側重明人的理解。由於中國和琉球國(沖繩,今屬日本)往來密切,臺灣逐漸浮現在明人的視野中。在處理十五至十七世紀初環中國海域的人群活動時,我們必須了解:明朝實施海禁,以及其後的局部開放海禁(隆慶元年,1567)是整個歷史進程的大背景。第二至第五節分別探討外人對臺灣的「逐步」認識。起初明朝出使琉球的封舟把臺灣當成海上航行的定位指標。隨著海寇問題的深化及侵犯範圍的南移,臺灣成為海盜的據點或海外的巢穴(以被稱為「東番」的西南靠海地區為主)。在明朝禁止人民和日本貿易的時代,臺灣成為中日貿易的轉運點;日本人靚靚它,幾度想加以招撫,甚至于以佔領。面對日本的野心,明朝士大夫認為它是大明東南海防的最前線雖不必為我領土,但也不能為他人所佔。其後,到東方尋找貿易據點的荷蘭人原本對這個(群)島嶼不感興趣,但在古領彭湖不逆之後,最後還是決定白領大員,將臺灣帶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路向。 臺灣這個島嶼,不論亞洲大陸的統治者如何認識它-夷洲也好,流求也好,或竟皆不是,它的土著民兀自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然而,它的四周來自不同歷史脈絡的發展不容許它「自外」於這一切。外人對這個島嶼的認識,從海上航行中的某個角度看到它的側影,逐漸因為各種具體的接觸而認為它是二個島嶼,或三個島嶼,最後大約在荷蘭人白領後,臺灣在外人的視野中才變成南北連成一氣的島嶼。此後,臺灣捲入複雜的歷史進程中,原本「遺世獨立」的島民則被動地進到對他們而言全然陌生的世界中。
- 期刊
日本在幕末維新期,西方列強勢力逼近之際,為汲取西洋近代文明,掀起「蘭學」風潮,而以各藩士族子弟積極吸收兵學、砲術,以備國防之用為最。當時「蕃書調所」為整備高水平教師陣容,聘任諸多具有西洋知識的「蘭學者」。其中算作阮甫(1799~1863)、塩谷宕陰(1806~1867)、佐久間象山(1811~1864)三人不但修習儒學,亦兼修「蘭學」同時對列強入侵日本產生高度危機意識,其間彼此思想主張立有激盪與變遷,對日本文明開化有其高度貢獻。 津山藩(今岡山縣)出身的算作阮甫於1839年出任幕府「天文方」幕僚,並受命為「蕃書和解御用」翻譯官。曾於1853年6月翻譯美國總統Millard Fillmore (1800~1874)的國書;同年7月,與幕府外交官川路聖誤(1801~1868)共同翻譯俄羅斯使節Evfemi Vasilievitch Putiatin (1803~1883)的國書。爾後擔任「蕃書調所」之首席教授,其精湛的外語能力與廣博的世界地理知識,影響了德川幕末之國防、軍事政策。 江戶出身的幕府儒官坦谷岩陰精通漢學,有「日東歐陽修」之稱,著有《隔 靴論》、《籌海私議》論及日本海防政策,曾是幕府「天保改革」之重要幕僚。岩陰向來關注清廷在鴉片戰爭時的應對措施及其帶給日本之影響,曾致力蒐集相關資訊,集結成《阿芙蓉遺聞》(七卷)及《岩陰存稿》。該著作之內涵最能反映其中國觀之形成過程。 佐久間象山為信州藩士,1853年美國培旦(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艦隊叩關日本時,奉命前往浦賀港觀察美國艦隊的動靜,曾提出海防諭向幕府獻策。象山從鎖國論的支持者轉變為尊王開國論者,《省警錄》即是體現其思想主張的重要原本,其「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前衛的世界觀,對日本的近代化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 本文於日本近代化的歷史脈絡中,從思想變遷的角度切入,比較三人的思想異同,並藉由解讀三人的原始史料之內涵,探究其思想體系之形成,同時分別論述三人在傳統儒教與現代文明糾葛的日本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 期刊
布萊斯•馬登(Brice Marded, 1938~)在1960年代末期開始作畫,被視為「低限主義派」,他很快就反對西方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繪畫已死」的觀念,並轉向中國書法尋求靈感,以復甦裝置於牆面之畫面觀念,作為繪畫之特徵。依照克里蒙•格林堡(Clement Greenberg, 1909~1994)的形式主義藝術批評,以牆面為畫面根基的概念,意味著完全平面、非三度空間幻覺的圖畫表面,其典型為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1912~1956)在1947~1951年間的壁畫式大尺幅油畫。格林堡的理論在1940年代末開始成為當代藝術論述與實作中最具影響力的說法,直到1960年代末才被質疑。馬登多方嘗試西方古典與現代藝術'又穿越一般看法中隔絕東方藝術之牆,從中國詩與唐代壁畫中的舞者,以及蘇州園林的湖石中汲取靈感。他重新發掘藝術史,因而重新解釋現代主義對畫面如牆面的譬喻,創造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物質與心靈主動。相對於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對繪畫的教條,馬登將不同的繪畫文化放在不容質疑的畫面空間,將世界的內容再度引進藝術的範疇。
- 期刊
比利時鐘鳴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2002年發表的”Methodology in View of Contact between Cultures: The China Cas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一文,是西方學界在中歐文化交流研究頓域中最新的理論分析。本文針對鐘氏運用的幾項理論及其解釋,提出問題,並作更進一步的討論。討論的目的有二: 第一、文化交流的方法論中,諸多概念的演繹,與近來西方學界文化史研究趨向密切相闕,因此,對其分析將有助於瞭解近年來蓬勃發展之中歐文化交流的研究,在過去以及未來如何讓跨文化的研究豐富歷史學的方法論。這個領域備受關注最有意義的一點,在於它為歷史研究開展了更多元的視野。本文將就人類學的理論如何影響跨文化的研究,交往互動的概念如何取代交流,以及文本性質的重新界定等議題,整合其他文化史理論作分析。 第二、近來中文學界有關中歐文化交流或基督宗教在中國的研究,由於衆多中國大陸學者的投入,對中國研究產生相當的刺激,但大陸學界的關注視野,與西方學界的文化史發展有不同的脈絡及結果。如何綜觀這兩方的發展而對未來提出展望,也是本文的目標。雖然本文主要以評析此文化相遇的方法論作出發,但其討論擴及廣義的文化史理論,對西方學界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亦將作部分的專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