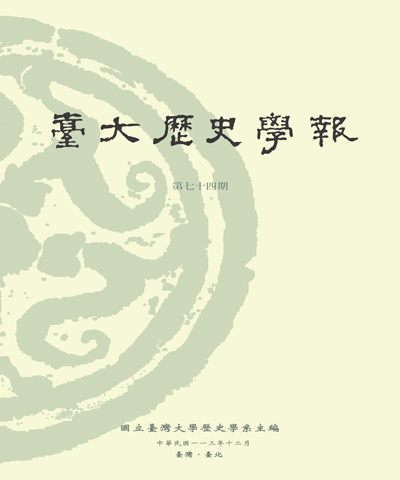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本文旨在通過對王陽明「四句教」的三次辯難的論辯措辭與論辯雙方所預設的「信念」進行共時態與歷時態的考察,管窺新儒學傳統(尤其是陸王傳統)演化過程中的權威(聖經、聖人、聖傳)與個體的體驗(心)之間、經典與詮釋之問、正統與創新之間存在的種種互動與張力,以期有助於把握儒學傳統的詮釋性品格及其相關問題。 全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全文的主要內容及主旨。第二節考察錢德洪與王龍溪就「四有」與「四無」所展開的爭論。第三節探討許孚遠「九諦」與周汝登「九解」之辯。第四節分析顧涇陽與管東淇就無善無惡所發生的爭辯。第五節則進一步辨析三次辯難之異同及其詮釋學義蘊。 本文認為,三次辯難之變化,既反映出明末思想演進的走向,也透露出各自相關語境的變遷。辯難所牽涉到的幾個不同的向度(聖人權威向度、經傳向度、功夫踐履向度、心-體驗向度)在不同的辯難過程中是不斷游移的,三次辯難也反映了儒學信仰共同體與其聖經文本之問的辯證關聯及其歷史變遷。
- 期刊
前人對明清之際士人殉死現象的探討,大都著重在觀察男性士大夫的生死抉擇,而甚少關心女性在這場劇變中的際遇。松江夏家的男性成員全部在明清鼎革之際殉國,但對明朝忠心耿耿的夏家男性,並沒有要求夏家的女性從死,反而希望她們能夠彼此照顧,努力存活,因為他們和當時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天下興亡乃是「匹夫」之責。和一般的印象不同,夏家婦女在國變之後,並不是以男性中心的妻妾婆媳關係來互相依存,而是由一個父系家庭拆解為數個以女性為中心的生活單位,並透過女性之間的關係,與其他的父系家庭結合成新的社會關係網絡。清人對夏家婦女的再現,多半著重在其守節撫孤的事蹟,但在抗戰以後,夏家故事的傳述者則越來越重視夏家婦女對抗清運動的支持和參與,顯示天下興亡「匹夫」之責的觀念,已經開始轉變。
- 期刊
對「直覺」的高度重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新儒家的共同點之一,儘管對「直覺」概念的詮釋和具體運用在各個哲學系統中有許多不同。本文的宗旨是分析梁漱溟先生如何借助對儒家經典和佛學的文化詮釋,在現代性批判的過程中,全面地闡發了他的直覺理論。 梁漱淇對現代性的批判集中到一點,是工具理性批判。他認為工具理性的高度擴張造成了西方的價值危機,包括在天人之辯上人與自然的嚴重對立、群己之辯上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困境、理欲之辯方面人的內心生活的貧困和分裂。為了救治世風,梁漱溟主張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資源,因此通過對《周易》和《論語》等儒家經典的獨特詮釋,以及對唯識論的發揮,抉發出「直覺」這一核心範疇。梁漱溟認為,直覺首先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擅長運用這種方法是中國古代形上學的重要特點;直覺也是獲得知識的方法,嚴格說主要是獲取有關意義或價值的知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直覺是倫理學的基本原則。因為直覺不僅關係到德性自我的確立,而且由於善的直覺包含了無私的情感,表現出強烈的驅動力和當下即是的自發性,由此進入實踐的領域。正如梁漱溟自述,其理論曾經受到某些西方心理學的影響,這是它表現為心理主義泛直覺論的原因之一。儘管梁漱溟的直覺論有不盡圓熟之處,但是他最早提醒人們注意直覺在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中重要地位、系統而全面地探討了直覺範疇,並且漸漸清除原先帶有的非理性主義成分,證明他不枉為新儒家的先驅。
- 期刊
本文主旨在論證日本江戶時代陽明學開創宗師中江藤樹以及其幕府末期的繼承者大鹽中齋特有的《孝經》學思想,認為二者將「孝」的思維,推尊到宗教性、神秘性的地位,極具有日本陽明學的特色。本文在第一節稍述研究日本陽明學不宜從中日近代知識份子在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之激情下,遮掩了真正的日本陽明學之特色。第二節分析朱子《孝經刊誤》以及對「孝」的詮釋所引發的後儒爭議。基本上朱子(1)對古文《孝經》的刊正,在於《孝經》原文中的「嚴父配天」會啟人僭亂之心。()2對「仁」、「孝」的關係,採取「孝」是「行仁」之「本」的實踐義,而非「是仁」之「本」的等同義,此項課題牽涉「仁」是否具有道德本體的超越性以及普遍性之問題。前項課題由藤樹破解之,後項課題則由中齋完成批判,並以「孝」取代「仁」作為總攝具有超越性以及普遍性的道德本體。故在第三節以藤樹對朱子《孝經刊誤》中有關「嚴父配天」思想會啟人僭亂之心的回應,並強化了「孝」的宗教性。第四節則分析中齋完成藤樹批判朱子「孝」思想的未竟之功,加強了「孝」的本體地位,扭轉了「仁」「孝」的道德本體之地位。最後提出簡單結論,並從本文針對日本陽明學對「孝」課題的發揚為契機,兼論日本陽明學具有宗教性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