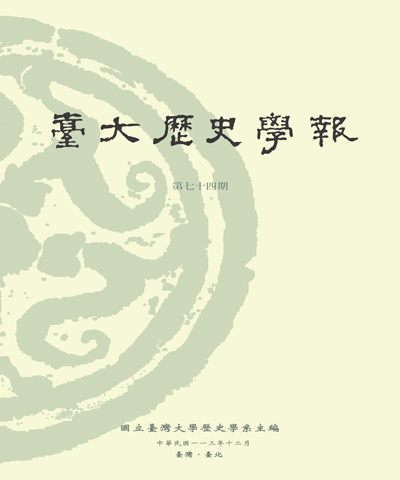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傳統東亞地區的士人,其學習過程是透過字書而認識漢字,乃至漢音,然後習讀童蒙教材(如《千字文》、《蒙求》等),再由《孝經》、《論語》入手,開始接觸儒家經典以及史書等。這種情形,其實也是中國自漢朝以來一般士人的學習過程。隨著東亞地區的政治、文化交流,使這個地區的教育事業,由私學到官學,逐漸呈現共相。這個共相,簡單說,就是儒教主義的教養。於是傳統東亞地區,以中國文化為媒介,自成一個歷史世界。
- 期刊
中國曆法在東亞的傳播,具有多重涵義及複合影響。然而,學術界過於注重其科學技術的層面,較少論及其政治和文化涵義。事實上,在近代以前,東亞諸國基本襲用中國的曆法,不僅把曆法作為先進的天文知識加以攝取,而且作為「尊奉正朔」的標誌以尋求文化認同。 基於上述觀點,本文在追蹤唐曆傳播日本的過程中,將百濟、新羅、渤海納入視野,以東亞文化聯動為背景探討中國曆法對日本政治及文化的影響。同時在汲取先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點討論下列幾個問題。 (一)中國曆法最初傳入日本的時間及途徑。百濟的曆博士王保孫於五五四年赴日傳授曆法,百濟僧觀勒於六○二年將曆本並曆法傳授給玉陳,其時百濟使用南朝梁的《元嘉曆》,可知南朝系統的曆法在七世紀前傳入日本。 (二)日本始用中國曆法有六○四年、六九○年兩說,前者推測使用觀勒帶來的《元嘉曆》,後者則是《元嘉曆》和《儀鳳曆》並行。筆者隊為,六○四年使用的是傳自百濟的舶來曆本,六九○年則是根據中國曆經自造的曆本。 (三)《儀鳳曆》之謎。日本沿用了七十三年的《儀鳳曆》,學界普遍認為是《麟德曆》的別稱,但在中國和朝鮮的文獻中找不出證據。根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麟德曆》八,《儀鳳曆》三」的記載,可知兩者卷次不同,推測中國歷史上存在過三卷本的《儀鳳曆》。
- 期刊
律令制是古代東亞世界的構成要素。目前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律令制研究,是關注日、唐律令的差異,藉此發現了日本律令的獨特性,並得以看出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固有形態。筆者是從田租、調庸等租稅制度著手,指出了在宗教的性格和在地首長的支配下,古代日本如何整合其固有共同體的性格以建構日本律令制的形態。此雖一方面被視為日本的特色,然亦具有東亞世界所共通的律令制之特色。因此筆者乃嘗試著思考:所謂古代國家的徵收租稅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 日唐的律令制或有少許的不同,然做為稅制核心之課役制度,皆是向正丁課徵均額的人頭稅。但是漢代的算賦和北朝的租調制,均是以鄉和三長為徵稅單位,即以全體為基準,按其口數和戶數來稽徵,鄉的役人和三長負有徵稅的責任。在唐律中亦復如此,民眾個人是否繳稅並不是問題,地方官所申報的課口數的虛假才是問題所在。人頭稅與其說是由各正丁所納入,毋寧是濃烈地帶有以鄉和里為賦課基準之意義。實際的徵稅乃委託里正和鄉長等基層的官吏,掌握戶口數的公文為計帳,日唐都是戶數、口數等的統計帳簿。唐代是以里正為中心,由鄉、里所調製,日本則是由郡司來彙整。國家為稽查其戶口之正確與否而設有貌閱的制度。 人頭稅作為一種課役制的本質,在於以課口數決定徵稅額的粗糙支配方式,以及由地方官根據計帳的課中數來承攬課役的貢納的組織架構。然而對照於唐代的鄉、縣、州之各階段多層級地包攬一定戶口數的貢納,日本則是以郡做為承包納稅的單位,里和國均沒有被定位為負責貢納的單位,如是存在著和唐的差異性。
- 期刊
日本德川時代儒者伊藤仁齋在整個日本儒學史中的重要性,乃在於他學問的反朱子學性格。仁齋的反朱子學性格,可見於其(一)、政治上群眾功利、事功的優先性(相對於朱子的個人道德心性的優先;(二)、人倫日用優先(相對於程朱的「格物窮理的優先性」);(三)、《論》、《孟》至上(相對於程朱的四書主義)等主張。若欲從整個仁齋著作體系中,找出一個仁齋與朱子二人對儒學的主張南轅北轍的根本歧路點的話,那麼,二人著作文獻中,漢字「實」字涵義,在中日語言問的微妙差異,可能是仁齋反朱諸多原因中最不可忽視的一點。這個論點的提起,主要是建立在「中日兩個民族所使用的漢文之間有著『表現語文』加上『思想義涵』兩重的落差性」的基礎上的。 仁齋在其著作中,充斥著諸多含有「實」字的名詞。而同一個漢字「實」字,日本語文與朱子學以降的中國語言相較之下,多出了日本特殊的社會背景、「功利主義」色彩;而少掉了本體論、形上學的氣味。特別是其中的「實理」一詞,雖然仁齋和朱子一樣,都在各自的學說體系中,對該一名詞賦與整個學說體系的基礎性的地位,但對該詞所賦與的義涵,仁齋與朱子有著根本性的差異。仁齋將「實理」定義成絕對排除抽象形上的成份;而強調維繫人倫網路通暢的感情成份的重要性。從日語中所用的「實感(じつかん)」一詞所指涉的功能出發,建立起維繫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為首的一切生物間親愛和諧關係的「感情繫鏈」。擴而大之,在仁齋看來,一切道理的虛實真假,唯有以賢愚不肖的所有人都能感知與否為準據;而聖人賢君地位的高下,每每以實際功利的大小為衡度的權標。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仁齋眼中,《論語》與《孟》、《學》、《庸》在儒門之學中不可同一等級而論;而文帝、唐宗在歷代賢君譜裡,可以比肩三代以上的堯舜禹湯。
- 期刊
將「亞洲」作為歷史、文化、知識有聯繫性的空間,並且從這一空間出發重新思考歷史、現實和未來,這無可非議。但是,這種關於「亞洲」的思想,歷史很長,在日本的明治時代即中國的晚清時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明治時代的「亞洲主義」言說及其發展,也追溯晚清至民初中國知識階層對「亞洲主義」的反應,指出雙方有相當大的差別,立場、心情和思路相當不同,而造成這種不同的背景,當然與雙方當時的處境有關,特別與各自的民族主義,以及各自的近代性追求有關。無論日本還是中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民族主義」都表現為對於國家整體的近代性追求,即通過追求富弦來凸顯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強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於是,民族立場和普遍價值就常常混雜在一起。因此,對於同一個「亞洲」,那個時代的中國和日本在認知上有相當大的差距。近年來,有的學者重新提出「亞洲價值」或「亞洲共同體」的意義,但是,我們還是需要追問,第一「亞洲」,是哪一個「亞洲」,是東亞,還是整個亞洲?第二,「亞洲」作為地理學的一個空間,如何可以成為一個文化認同空間?第三,日本所認同的「亞洲」,是否就是中國和韓國也都認同的一個政治或文化共同體?第四,「亞洲」究竟是一個需要建構的共同體,還是一個已經被認同了的共同體?換句話說,它是已然的歷史,還是希望的現實?
- 期刊
藉著檢驗《晉書》(西元六四四年完成)對羌人後秦君主姚興於三九九年稱天王記載的矛盾,並參照四○○年左右佛教在中國所流行的教義與神話,佛教文獻對姚興的記載,以及佛教文化圈內的君主觀,本文指出姚興稱天王乃是受佛教帝釋的啟發,而非來自中國古典《春秋》的天王說。他的統治行為也與佛教的帝釋觀吻合。然而,佛教的天王觀和漢朝以來外儒內法的統治治術背離,使得後秦政權在他死後迅速瓦解。本文為北朝胡人君主使用天王號提出另一個新的解釋。
- 期刊
今天的日本法是在移植西方法的基礎上形成的,但是它又不同於西方法具有自己的特色。究其根源則在於:日本傳統的法文化在日本近現代法的形成發展過程及今天的法律生活中仍然發揮作用。因此,要瞭解今天日本法的獨特性,又須追溯日本古代法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