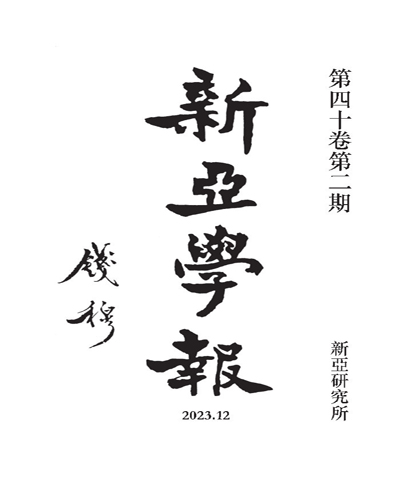
新亞學報/New Asia Journal
新亞研究所,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清末四川重慶府巴縣的團練,是位次較低的「國家代理人」,團練得到官府這個「委任人」授予權力,團練這個「代理人」也形成自己的追求和目標。團練在「社會的安定化」和「社會的流動化」這兩個向量之中,有截然不同的表現。在「社會的安定化」階段,意即在戰亂頻仍、人人自危的時候,團練協助衙門,提供社會治安這項寶貴的公共財,例如逮治盜匪、禁止私宰耕牛、禁止盜伐竹木,管束外來人口、仲裁居民糾紛等等。這時,團練的活動一般是得到官府和居民的支持的。但是,在「社會的流動化」階段,意即在社會秩序相對穩定、人們感到時局太平的時候,團練作為社會治安這項公共財的提供者,就顯得沒那麼必要了,官府對於團練充滿猜忌,居民對於團練也喪失好感,因此團練的存在本身就會產生紛爭,紛爭往往圍繞著徵收團費、配備武裝這兩大問題而產生。巴縣團練的情況,可以說是「委任人-代理人困局」的案例之一。
- 期刊
《二區舊五團鄉志》是民國時期江南海濱地區編印的一種鄉鎮志,本文在梳理編纂者及其身分背景的基礎上,探討該志所表現出來的鄉土敘述方式和歷史意識的時空脈絡。南匯縣五團鄉地處海濱,明時設灶戶,鹽業一度為地方主要產業,但隨著沖積地不斷向東延伸,逐漸停產,鹽田以及新沖積地被開墾為棉田和稻田。清代第一批遷入沙田地帶的移民,在清代中後期通過沙田的報領積累了大量土地,並以其作為經濟後盾,引進儒家禮儀文化,加強了父系血緣組織的力量。他們的後代還吸收了與科舉相關的主流文化。清朝中期以後,當地出現了幾個擁有科舉功名士人的有力家族,他們通過詩文圈子等士人網絡加強聯繫,並掌控本鄉的事務。清末,出自有力宗族的士人通過引入近代學校制度和舉辦地方自治事宜,積極推動基層社會的現代化。儘管如此,他們的各種出版活動和著作證明科舉時代的儒家主流文化仍然是他們的活動和言論的基礎。雖然聽起來有點弔詭,但也可以說他們的活動和規範意識是被嵌入在「遲到了的近世」中。隨著清末科舉的廢除、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引進、各種西方知識的傳播,以及新式知識分子的出現,基於「近世」規範意識而成為推進各種現代化事業的士人階層,在1910年代末迅速面臨世代交替的窘境,他們在日趨邊緣化的過程中,被迫證明自己的正統性。包括鄉鎮志在內的各種著作出版即是一種因應邊緣化的自我主張形式。
- 期刊
本文以清末民初的莒州為例,重構當地鄉民依靠士紳地主來抵抗捻軍侵擾的過程。自清朝中葉開始,莒州出現了以大店莊氏為標誌的大地主宗族。咸豐末年到同治年間,捻軍四處流竄劫掠,嚴重威脅華北的社會秩序。莒州也遭到捻軍進攻。起初,鄉民組織鄉團對抗捻軍,證明無效之後,轉而修築零散的「圩」、「寨」、「堡」,大部分鄉民逃亡山間;這一招仍然難以對付捻軍的侵擾,於是轉為大規模依村立寨、堅壁清野,終於打退捻軍。在此「地方軍事化」過程中,莒州出現了以士紳地主為中心的、跨越階級而凝集起來的菁英集團,包括大店莊氏、張家莊張氏、停溝于氏、北汶王氏、莒北管家窯管氏等。
- 期刊
八關齋,佛教在家教徒規範的一種,其名目和條文、受持期限,以及天神巡查、鬼神護持等相關內容,早見於《阿含經》及相對應巴利語經篇,可見在佛教成立不久,八關齋之說已趨完備。其後的漢譯佛典,對受持威儀、授受者身分、受持日子和支數等,說法更多;並就不非時食是否八支之一,產生爭議。由於受持八關齋簡便靈活,融入成為漢化佛教以至中土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元素,疑偽佛經亦多提及,凡此令有學者以為八關齋實受中土祭祀傳統或道教影響才成立。八關齋雖耳熟能詳,但未見全面和細緻的探究。本文除對漢譯佛典的相關記述作通盤整理和研究外,並以之為基礎,檢視八關齋是否源於印度,期望對佛教的在家律制及其與中土關係,有更清晰的瞭解。
- 期刊
明萬曆十四年(1586)秋杭州西湖的南屏社集,由文壇重要人物汪道昆(1525-1593)擔任盟主、活躍的商人子弟卓明卿(1535-1594)擔任東道,雲集二十多位東南名士,創作一系列詩文作品。筆者詳考史事,細讀文本,爬梳細節,重現是次社集的文化、政治、社會等多重面相。它既是具體的、受制於達成條件的遊樂活動,又是遵循社集傳統的行為藝術;既是文學才華和浪漫人格的展示,也受社交規則與禮儀階序的宰制。在南屏社集上以及隨後寫成的相關作品,出於多人之手,且遊走於作為事件的社集和文學文本構築的社集兩端,互相彌合又互相「拆臺」,不無扞格之處。自晚明迄今,造成兩種常見誤解:或將王世貞(1526-1590)作為實際到場的賓客,或將萬曆十一年(1583)中秋的西湖之會和十四年秋的南屏社集混而言之,在此基礎上闡發其文學文化意義。筆者認為,上述誤解與其說是源於對文獻和史事的誤讀,不如說更近於汪道昆為主的社集賓客在落筆之際的有意營造。不在場的王世貞具有特別的意義:他既是社集的特殊參與者,也是社集文字創作時的預設讀者。將他的存在和注視納入考量,南屏社事和文字的意義才能得到更完整的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