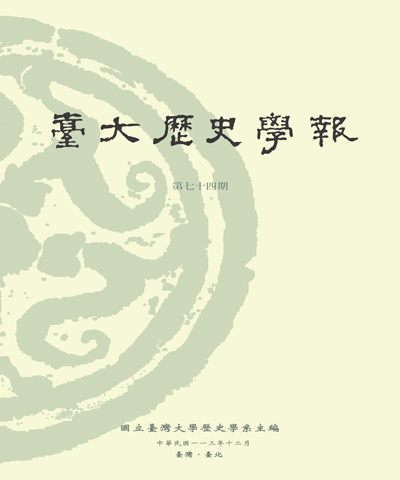
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現有針對軍統組織的研究,大多以戴笠(1897-1946)為核心。然本文目的在於闡述如何運用地方社會研究的觀點,思考不同時代的新興人群組織──福州地區救火會與軍統,涉及地方政治運作與20世紀歷史發展的複雜關係。坊間廣泛流傳軍統神秘冷酷的殺手形象,且過往對軍統與地方政治發展的討論,多從黑幫地下社會與政治暴力等角度切入,導致刻板印象的認識有餘,但對實際運作狀況仍缺乏了解。本文將以由下到上的歷史觀點,討論1890至1952年的福州救火聯合會與軍統福建省閩北站的發展歷程。從人事發展角度,探明軍統局與19世紀末以來福州地區最重要的人群組織──救火會,雙方如何達成結盟,並重新思考福州地方政治的發展歷程。
- 期刊
身分辨識是現代政府治理的重要行政基礎,個人身分倘無法被識別、追蹤,不僅政府部門難於治理,私人企業也無從提供服務。本文以上海的身分辨識系統如何精進化為例,檢視近代中國政府增強身分辨識能力,使人民臉孔清晰化的過程。具體分析項目圍繞在戶口普查、清查與身分登記所形成的辨識行動,以及所製造的文書檔案、身分憑證,如何具有識別人口的功能,又如何被施予統治意圖,例如進行選舉、防範治安、分配糧食等。研究發現,八年抗戰時期不僅沒有中斷上海身分辨識系統的發展,反而成為重要的積聚階段,銜接戰前上海市政組織已有的身分辨識機制,與戰後國民政府統一的全國身分辨識系統。戰時上海的占領政權是在治安大旗與軍事武力的後盾下,以保甲編組和糧食配給為強制力,提升市民證辨識人民身分的效力。然而,戰時此一帶有壓迫性的身分辨識系統,也對戰後國民政府在上海的統治,留下制度遺產與歷史記憶的雙面刃影響。一方面,國民黨認知統一全國身分辨識系統的重要性,因此推行國民身份證;此舉卻也喚起上海市民在日本占領時期遭到壓迫的記憶,導致國民身份證推行不暢。綜觀20世紀上半葉身分辨識系統在中國精進化的歷史,受戰爭強制力推進的程度,遠勝過訴求自治選舉、社會救濟等增進人民福祉的力量。這對1950年代海峽兩岸政府的戶口政治,都產生影響。
- 期刊
蕭縣位於江蘇省西北端,地處蘇皖交界地帶,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是抗戰期間國、共、日偽三方角力的前線。抗戰勝利後,蕭縣既有軍政格局被打破,國共關係劍拔弩張。黃體潤(1896-?)曾長期擔任豐縣黨、政、軍要職,對付中共也頗有心得,1945年底被任命為蕭縣縣長後,積極調整縣政府和區鄉人事,強化基層組織,鞏固國民政府控制區。與此同時,中共也盡力在蘇北擴張勢力,對蕭縣構成威脅。在國軍支持下,蕭縣縣城和全境陸續克復,黃體潤隨即在全縣清剿殘匪、健全行政體系、發展民眾自衛隊,著力鞏固縣政權。地方秩序逐漸恢復後,黃體潤推進縣政建設,如設立各種專門委員會、整編地方武力、訓練基層幹部、清查土地、實行二五減租、發展生產事業、組織和成立縣參議會等。這些舉措的目的是通過改善縣域內政治、經濟、社會狀況,重建和鞏固國民黨在蕭縣的統治秩序,作為戰後「建國」事業的一部分。國共大勢是影響戰後蕭縣歷史進程的關鍵因素,「勢」的變化決定「為」的取向,當國共關係急遽惡化時,縣政建設事業只得中斷,以剿匪為重心。戰後的蕭縣,是國民黨地方政權勉力維持、努力建設的一個典型案例。然而,「小歷史」終究敵不過「大歷史」,隨著國民黨在徐蚌會戰失敗,蕭縣之發展徹底改觀。
- 期刊
古埃及的三段中間期皆為王國與王國之間的過渡期,它們的歷史通常較模糊不清,因此有不少歷史學家和埃及學學者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事實上,隨著大量文獻資料的解讀和考古挖掘的物品出土,20世紀初以來,學者們將其拼湊,已著手重建這三段中間期的歷史過程,雖未百分之百精準,但已能看清大致樣貌。本文首先概述三段中間期的歷史發展,其次研究它們的起因,最後探究它們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透過以上探索方向來反思三段中間期的歷史,藉以打破前人對古埃及中間期之「黑暗」的刻板印象。
- 期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於1919年年初召開巴黎和會,以安排往後的國際秩序。伊朗在大戰之前,受到英國自南方、俄國自北方的壓迫,本就致力於擺脫兩強權的束縛,在戰爭時期也宣示中立;但其西部領土卻受到英國、俄國與鄂圖曼帝國交戰的波及。此時俄國因蘇維埃革命,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退出伊朗,戰勝的英國得以在伊朗成為單一霸權。此外,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提倡的「民族自決」原則,讓伊朗藉機爭取自我權益。是故,伊朗籌組代表團前往巴黎,欲參與和平會議,希望能獲得賠償以及國際承認伊朗的獨立地位。不過,英國稱伊朗為中立國,不得進入巴黎和會,而且唯有英國能夠協助處理伊朗問題。伊朗首相維蘇克道拉(Vosuq al-Dowleh, 1868-1951)評估時局後,認為與英國達成共識,或許是改善現狀的唯一方案。1919年8月,維蘇克道拉與英國駐伊公使考克斯(Percy Cox, 1864-1937)簽署《1919年英伊條約》,英國承認伊朗為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國家,也協助伊朗改革軍事與財政。儘管伊朗代表團最終未能進入巴黎和會,原先的要求卻透過該條約而達成,而英國藉由主導伊朗的軍事與財政改革,得以維持在伊朗的絕對優勢。該條約雖然招致伊朗國內外輿論的批判,卻是兩國各自尋求最大利益之下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