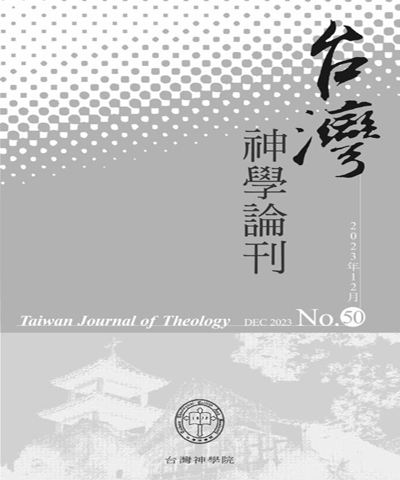
台灣神學論刊/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台灣神學院,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只使用一種研究方法,不足以詳盡地分析保羅的書信。本文試圖以寫信學(epistolography)和修辭分析(rhetorical analysis)共同攜手合作,藉著保羅寫給加拉太人的信,更進一步了解保羅與加拉太人之間的互動。更具體的說,對於保羅的說服策略,本文提出了一個不同以往的詮釋。本文基本假設,加拉太書的修辭類型是屬於勸說式(deliberative genre)。根據亞里士多德,此類型的主要說服手段是集體意識(ethos)(角色,也就是演說者的身份與權威對聽眾的影響力)。要是這個假設成立,那麼就加拉太人接受保羅的論述來說,集體意識應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本文以快速瀏覽加拉太書文本,相互交織來凸顯集體意識的說服功能。
- 期刊
以斯帖活在以男人為主導的波斯帝國、社會、家庭的男人世界中,面對王權、男權、父權的三重打壓。在這三重打壓中,以斯帖只要固守本身的處境不跨越界限,保持「閉口不言」,就可相安無事。然而,末底改與哈曼的私人糾紛卻在男人世界掀起軒然大波,甚至為猶太人招來滅族之災。末底改遂以養父身分,要求置身在王宮的王后以斯帖,冒險未召擅見王。此舉頓時迫使以斯帖陷入三重張力之中,舉步維艱,不知當做何抉擇。也就在這關鍵時刻,以斯帖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主動,更充分運用智慧,設下謀策,在三重張力下表現出三重忠誠。最終,她不僅解救猶太同胞免遭哈曼的毒手,也從當時的王權帝國、男權社會、父權家庭的三重制度或秩序中逆轉,從而在帝國、社會、家庭中表現出巾幗不讓鬚眉的「女強人」精神和作風。
- 期刊
近二十年來,在當代基督教學界裡,「公共神學」已經蔚為一個新的運動,值得關注。本文旨在回溯這個神學運動的歷史脈絡,包括清教徒運動、蘇格蘭啟蒙運動、歐洲的政治神學、北美的公民宗教傳統等。一方面探討它的形塑過程和歷史面貌,另一方面則要指明,基督教在公共領域裡的「涉入和參與」一直是內蘊於其自身傳統的特質。換句話說,本文意在指明,基督教自始就是一個公共宗教。只不過這樣的特質,必須要等到近現代後才逐漸明顯浮現,特別是受到加爾文所開啟的改革宗傳統的深厚影響。在二十世紀中葉後,更在有識之士的推動下,形成一個明顯且有意識的神學運動。
- 期刊
靈魂的觀念不斷受到現代聖經學者與系統神學研究者的質疑,這些人認為靈魂這一觀念是從希臘植入古近東思想界的。不管怎麼努力修正這個「彎曲的教義」總是遭到阻力。就算現代的神經心理學能提供神學家一個超越靈—體二元論之人學的科學基礎,依然有其顧慮:(1)神學不該受制於簡化的科學及其對靈魂的否認,(2)基督教人學應保持其傳統觀點,強調靈魂不屬物質的重要性。本文將考察最新趨勢的非簡化物理學及現代神學,以便:(1)提供這個論題的背景,(2)說明自然科學不是神學的敵人,以及(3)論述基督教人學主要教義─「上帝的形像」、「罪」,救恩之完成乃經由上帝國所帶來的社會轉化與終末「復活」的盼望─因柏拉圖式之基督教的靈魂觀而遭到誤解。最後以(4)簡要的考察重估靈魂主張的教牧關顧作結。
- 期刊
加爾文一生的追求即是榮耀上帝,他所做的一切也都只為了上帝的榮耀,而榮耀上帝的舞台就是今時今世。一個被罪惡毀壞又充滿失序及混亂的世界,如何能榮耀上帝?加爾文的神學促使他竭力恢復上帝原有的創造秩序,而「秩序」立時成為榮耀上帝最有力的方式。然而,因為罪的產生,已決定性地改變了上帝在自然中原有的創造秩序。因此,秩序的修復與維持,就是尊崇上帝。秩序對加爾文而言,是具有神聖性及宗教性的。加爾文的秩序觀帶有強烈的宗教意識─秩序作為宗教及體制的思考點;「上帝的秩序」則成了加爾文一生所關注的議題。本文嘗試整理加爾文《要義》的秩序觀,並參考他其他的作品,如聖經註釋、講章、書信和各式文章,再加上其他學者的觀點同步合參,以探討加爾文秩序觀。「上帝的秩序」包含:宇宙秩序、救恩秩序和人為秩序。這三部分正是《要義》的核心思考,即以上帝為中心的秩序觀、以基督的救贖作為恢復神、人、世界秩序和諧之根本。
- 期刊
本論文試圖有系統地瞭解「舊講道學」與「新講道學」的不同。為了更具體的說明新、舊講道學在方法論上及教學內容上的差異,筆者分析並比較二本具代表性的講道學教科書─John Broadus在1870年出版的《講章的準備及傳講》("A Treatise on the Preparation and Delivery of Sermons"),及Fred Craddock在1985年出版的《講道》("Preaching")。倘若如一些學者所言(如:Lucy Rose),二十世紀上半期是Broadus的時代,他對講道的瞭解是「當代講道學理論所反對並建構的主要背景」的話,那麼1970年代的「新講道學」所反對的並不是「舊講道學」的「原型」,而是一個被簡化、甚至被曲解的「變型」,即在歷史的進程中Broadus的講道學理論遭到後人的修改、誤解、或忽視。然而,當代講道學者卻忽略此一事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大多數學者並非直接從Broadus的教科書文本進行研究,而是採用第二手資料,以致於造成人云亦云的現象,並對「舊講道學」作了不客觀且不正確的批判。所以,本論文不僅提供講道學老師一個具體說明「從舊講道學到新講道學的演變」之教材,更修正了當代講道學對「舊講道學」所持的一些錯誤觀念,同時也證明了「第一手資料的研究」在講道學研究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