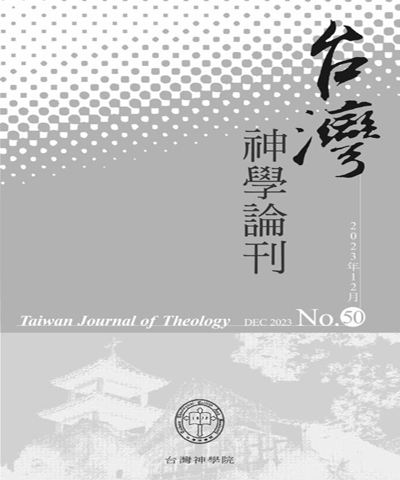
台灣神學論刊/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台灣神學院,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在路加福音中有些最重要的基督論之陳述,是出現在用餐的經文。在耶穌拜訪撒該轉化他生命之時,祂啟示自己來的「目的」:「人子來是要尋找和拯救失喪的人」(19:10)。在福音書較前面的經文中,耶穌將自己來的「方式」和施洗約翰做對照:約翰來的時候禁食,但「人子來,也吃也喝」(7:34)。藉著同桌用餐,耶穌展現幾種不同的角色:最典型的一種是作為用餐的客人,除此之外也扮演主人,或描述自己為餐桌的僕人。在前一期的文章中,筆者已介紹過耶穌成為稅吏和罪人(5:32;7:34;15:1-2;19:1-10),以及法利賽人(路7;11;14)的客人的角色。在這期的文章,則欲闡明耶穌如何向祂的跟隨者展現為「客人」的角色:到家拜訪兩姊妹時,祂帶來自己的話語作為禮物送給她們;拜訪兩個門徒時,祂把他們的絕望變為喜樂(路10;24)。有時,耶穌也扮演用餐時的「主人」:祂供應豐盛的食物給在荒野的數千人(路9);與門徒一起,祂主持守逾越節的晚餐,在那裡祂用餅和杯的分享承諾自己的生命給他們(路22);在以馬忤斯村莊,耶穌受邀成為兩個門徒的客人,事實上,祂是扮演成主人的身分,而且祂的擘餅使得他們能夠認出祂來(路24)。最後,在逾越節晚餐的經文中,耶穌呈現自己為「僕人」的身分,祂不只在餐桌上服事門徒,還保證他們和自己會同坐在上帝國的宴席(路22)。作為客人的耶穌引介了上帝救恩的臨在;作為主人和僕人的耶穌期望未來在上帝的國裡,作為宴席君王的角色。根據路加福音的記載,當耶穌在餐桌加入人們時,祂給予人們一個具體經驗救贖的機會。因為死裡復活後的耶穌會繼續和跟隨者同桌團契-作為他們用餐時看不見的客人,祂繼續臨在人們當中引介救贖。
- 期刊
保羅說自己不用智慧的言語傳福音,好像他拒絕使用修辭來傳講信息,然而,Karl A. Plank發現保羅使用修辭,還以反諷修辭作為建構福音信息的核心。對於Plank的觀察,筆者也發現保羅確實使用修辭來處理哥林多教會的問題,但是,筆者認為主要的修辭風格不是反諷,而是吊詭修辭。反諷修辭是指作者的實際意思恰是字面的反面意義;吊詭修辭則是作者同時保留字面的正反兩面,藉著這種正反共存的矛盾衝突,引導讀者尋找隱藏在這正反共存之後的真理。從這定義中,我們發現吊詭修辭也具有反諷的功能,因為它也保留了字面的相反意義。因此,當我們進行分析時,必須判斷保羅是否保留字面意思,如果只有反面意思,就是反諷修辭;如果同時又保留字面意思,那就成為吊詭修辭。透過修辭批判的論據分析,筆者發現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18節至四章21節以十字架的吊詭作為立論的範型,採用豐富的吊詭修辭作為勸告的策略,一方面藉著吊詭修辭的反諷效果顛覆哥林多教會的觀點,另一方面同時又藉著正反共存的矛盾引導他們思考隱藏的真理。保羅以基督十字架的吊詭作為判準,勸哥林多教會棄絕地位的追求,效法保羅為基督的緣故成為愚拙、軟弱與卑微,按著各人從上帝領受的恩賜,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地建造教會。
- 期刊
雅威對先知的呼召,是先知職事的基礎。本論文嘗試透過舊約聖經中先知書的四位先知與他們的呼召敘事經文,來探討先知書中的人觀。藉著先知以賽亞、阿摩司、耶利米、以西結的時代背景、呼召敘事與其中信息對人的探討,認識到雅威對先知們的呼召敘事,雖然有類似性(例如:皆與嘴的功能有關),實際上並沒有固定的模式。先知是透過與「他者」(雅威)的特殊經歷後,重新對自我有新的眼界與先知身份的肯定。雖然先知與雅威的相遇是個人性、隱秘性的呼召經驗,先知卻是在廣袤人群的歷史脈絡中接受呼召。本論文一方面呈現,因著雅威的支持,先知得以承接那義無反顧的任務,向額堅心硬的人群忠實地宣告雅威的信息。另一方面,與王國時期的先知比較起來(以賽亞、阿摩司),上帝的靈在以色列亡國、被擄期間,似乎是更加明顯地做工在人的身上(耶利米、以西結)。
- 期刊
筆者主張以浪漫主義的觀點詮釋布胥納的講道,將能更精確解讀他的講道及神學中所呈現的不一致性。深受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布胥納認為神學是「基督教經驗之系統表達」,強調宗教經驗對真實信仰的重要性。以布胥納的理解,信仰絕非停止的狀態,乃是持續進行的過程,他自己的靈性歷程也同樣反映出四階段的發展。因此,筆者提出一個研究布胥納的講道之新方法,即將它置於此四階段的宗教發展之架構下解讀:1802-1830、1831-1847、1848-1860,及1861-1876。如此一來,它將精確指出布胥納的宗教經驗如何影響他的講道,以及在靈性發展的歷程中,他的講道如何逐漸轉向福音佈道性的講道。關於這後者,正是長期以來被學者們忽略的一項重要事實。這種對布胥納的福音佈道性講道之新發現,將糾正兩個長期以來關於布胥納的講道之錯誤看法:第一,由於布胥納早期對奮興主義的嚴厲批判,許多人因而誤解他完全否定重生的必要性。第二,傳統將布胥納與芬尼作為對照的二分法(基督教培育的講道vs.福音佈道性的講道),也是對布胥納的講道之錯誤解讀。本研究將幫助當代講道學者能更正確地瞭解布胥納所留給教會的講道遺產,並重新評估他在美國講道歷史上的重要性。
- 期刊
本文寫作的目的有四:(一)幫助傳道人、牧養同工認識「教牧關顧與輔導」的角色和定位。鑑於多年來,教牧關顧與輔導在台灣的教會界不只身份不明,牧者的認知不一,即使許多神學院校陸續開設教牧輔導、教牧協談的課程或科系,也未必明白何以「教牧關顧與輔導」須並稱成為一門課程。(二)澄清教牧關顧與輔導的緣起,它不只是一項事工,更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二十世紀心理學的興起,帶來教牧關顧與輔導核心價值的混淆,產生許多誤解和偏差。(三)心理學和神學在教牧關顧與輔導中扮有重要的角色,但兩者不相屬,各自獨立。教牧關顧與輔導的根基建立在神啟示的原則,而非人本主義的牧養觀。(四)教牧關顧與輔導需從個人、歷史和失去的定位中,重新找回身分的認同,特別是面對當今人類問題叢生,許多受苦者需要教牧關顧與輔導者的幫助。為回應人的問題,當代心理學有助於對人類內心活動的瞭解,心理諮商理論為教牧關顧與輔導提供實際的幫助,但無法解決人類終極的問題。教牧關顧與輔導處在心理學、基督教信仰和神學中,如何在既有的基督教牧養傳統和豐富的屬靈資產上站立得穩,以成為教會的祝福,實在值得關切。然而,危機是轉機,當人們意識到教牧關顧與輔導失去身分認同的危機時,願意奮力重新拾回其身分認同,將使教牧關顧與輔導成為教會的祝福,以服事這時代受苦的百姓。
- 期刊
面對死亡失落,是人一生無法避免的事。然而面對喪失親友的驚慌失措,無助卻成了生命中的一個障礙。成為一個陪伴者,要了解在哀傷的歷程中需要許多的等待與陪伴,不僅是需要有認識哀傷的知識,更需要有對哀傷者有溫柔謙卑和尊重的態度。本文目的在對於一般哀傷歷程、意義治療與敘事治療進行文獻初探,以整理出實用性內涵,包括認識哀慟、尊重哀慟、允許哀慟經驗、適應逝者不在的環境與找到個人化意義與重建新意義的架構。研究者發現連結意義治療,與敘事治療兩者治療的理論,在使用上不但能夠很完整來檢視哀傷中失落的意義,還能以口語的敘說重建新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