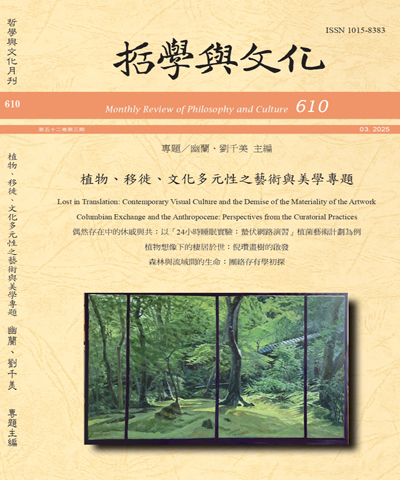
哲學與文化/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一般而論,宗教現象學係以現象學來研究宗教。職是之故,宗教現象學乃是現象學運動的一部分。然而從人類的經驗觀之,觀察、蒐集、探討宗教現象宛如宗教般古老。是以,討論宗教現象學的問題,勢必從其基本的面向著手,才能免陷於片面的獨斷立場。 本文首先描述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現象學方法和主要因素和結構,並探究胡氏平常很少提及的主題:宗教觀。 雖然胡塞爾 奧托(Rudolf Otto, 1869-1937)均強調宗教的「自成一格」(sui generis)但胡氏以非神的哲學態度來看宗教;而奧氏卻認為宗教現象惟有對信徒才有其真義。由此可見,兩者對宗教的「本質」顯然見解不同。 其次,我們探討脈絡中的宗教現象,以舒茲(A. Schutz)、伯格(P. L.Berger)以及盧克曼(T. Luckmann)作為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代表。最後,我們重建宗教現象學的「本質」和「脈絡」的基礎性,它們不僅不能分開或者對立,而且是互補、互動的。這樣的宗教現象學方能成為宗孝教交談的基礎:即有深度(本質)又有廣度,亦即 蘊含對「圈內」(insider)和「圈外」(outsider)的了解。
- 期刊
本文比較康德與羅耐剛的知識論,在康德的知識論中,悟性只對感性顯象加工,理性則只對悟性加工。而且惱性與理性兩官能不是直曲的官能,因此不具忍知性格,對對象不提供新的實在的認知。所以人的認知方式決定於感性直觀。感性直觀所獲得的是顯象,因此人能夠認知的只是顯象,而與物自體無關。 在羅耐剛的知識論裡,我們的認知官能是一個要達到存有的認知官能,其主觀的先驗條件是先驗的存有概念。我們認 知官能自始尋求存有,結束於肯定存有。所謂認知的真理是,我們的理解與實在一致;而不是康德所認為的,在於認知與主體先驗法則一致。因為限定對象之意義與範圍的,是認知的意向性,而不是那個直觀。
- 期刊
海德格質疑西方傳統形上學遺忘了作為存有「遮蔽面」的「無」 ,同樣的「無」的問題也一直困擾黑格爾,「有」與「無」之弔詭更是他辯證法的核心概念,有別於西方「實體學」的傳統,「存有」的意義在黑格爾體系發生了逆轉,在《邏輯學》中<必須用什麼作科學的開瑞?>一文,黑格爾論及哲學的「開瑞」(der Anfang)時提出了「純虛無」(das reine Nichts)的概念作為「存有」的第二性格,並論述「純存有與純虛無同一」的觀點。他反覆的使用「純粹」(rein)這個概念來彰顯「純存有」在開始階段的「虛無性」,以突顯「無」在存有矛盾辯證過程的重要角色。本文扣緊黑格爾所論述「純有」(reines Sein)、「純無」(reines Nichts)、「缺如」(Mangel)、「第三者」(das Driffe)、「變」(Werden)等概念,希望揭示黑格爾如何立基於西方Logos的傳統來探討「無」的存在學意義。他扣緊Logos的傳統,闡釋理性活動是以揚棄知性為基礎,企圖建立一套融合「有無」、「正負」矛盾辯證的「統一哲學」。
- 期刊
因應高齡化社會的來臨,以及生命權利意識的高漲,台灣這近十年來,生死教逐漸受到重視,語人亦逐次習慣討論過去視為禁忌的話題,譬如死亡本身;本文試圖探討「生之愛欲」與「死亡」兩者集結性思考後產生的關聯,我們將分別由生命的極熱和極冷兩端,從缺乏、忘我、以及永恆諸視點呈現它們客自所到達的視域,由不同的兩極所產生的激盪,或許其豐富性正是吾人原先企想莫及的。再者,兩性的觀愉一貫降低了愛欲的質感與深度,本文中將以死亡的角度重現其莊嚴感,以讓世人了解愛欲的對象是多層次的,且愛欲的真相受社會壓力層層綑綁無法如實呈現,一般人很難體會我們承受了哪些社會制約,除非藉著死亡引導,方能一一揭開愛欲的神秘面紗。
- 期刊
康德倫理學乃是宗教-倫理學、亦即道德神學(Moral theologie),它是現代性的個體信念倫理(Ethics of conviction),後者則是現代性宗教主要依託形態。圓善(The Highest Good)論是康德論理學中心。德行與幸福兩個世界統一的信念,要求一個超越日常時間的無限時間,它與基督教末日觀念相關,圓善由此護得宗教信仰性質。這一結構顯示了現代人文主義的最高限度,同時標誌著現代性宗教的起碼位置。
- 期刊
本文討論並肯定了思辨歷史哲學的基本特點、歷史起源及主要內容。思辨的歷史哲學把歷史看作是一個有意義的整理,是用世界觀解釋歷史。它是關於歷史的形而上學研究。與分析學派相比,它同作為「愛智」的哲學更具有連績性。然而,歷史哲學畢竟不是希臘人的創造。它源於基督教,只是近代被世俗化了。從古希腦到基督教,伴隨看從周期性模式到進步模的軒札。但基督教的進步理論被包衷在天意論中。近代歷史哲學則把天意還原為自然和理性。盡管缺乏實證證據,盡管人類生活的意義並不完全取次於歷史的意義,但開於歷史進步及意義的形而上學理論確乎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思辨歷史哲學與人類有意義地生活共始終,不會也不應當消失。
- 期刊
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 中認為,基督宗教作西方非會的基礎。他特別強調基督宗教包含內在的動力使全社會能不斷的進步。而且基督宗教有能力統一社會,而跨越具體文化的領域。另外,梁漱溟認為,為了得到這個社會目的,人要付出的代價太重,而且從儒家的角度來看宗教的路違背人的道德理性。因此,梁溟肯定中國與西方走不同的方向。兩方面只能互相學習而更忠誠於自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