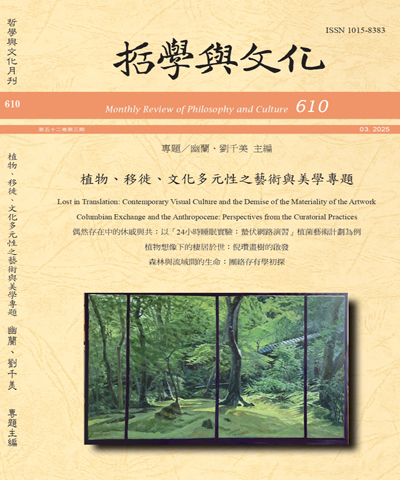
哲學與文化/Universita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 期刊
儒家的義利之辨,不但涉及個人進退、取與、榮辱的道德觀,也涉及群體生活的公共領域。前者屬個人德性倫理學的課題。後者涉及社會報酬會理化,個體權利的保障與治生問題上合理利益之追求。陳大齊先生善於辨名析理的名理分析。他對先秦儒家,特別是對孟子義利之辨的研究精微細緻,成果斐然。本文對陳先生針對先秦儒 家典籍中的《論語》、《孟子》、《荀子》所做的「義」、「利」概念之分析,學者們對「義」、「利」關係不恰當的說法之檢討逐一處理,且予以評價,期能將陳大齊先生這一研究成果再現於學界,足被青年學子們識。
- 期刊
著名的亞理士多德學者大衛‧羅斯(Sir David Ross, 1877-1971)在當代倫理學上是一個「義務論者」(Deontologist)。主張吾人之遵守道德是做人的責任,而非為了任何功利或效益──此一思想,近於漢儒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明其道不計其功。」 本文將依據他的主要著作《正確與良善》(The Right and the Good, 1930)和《倫理學的基礎》(Foundations of Ethics, 1939) ,來探討其在當代倫理學裏頗為重要的概念「初適責任」(Prima Facie Duty)。本文之敘述,將以「由小而大」的方式。首先詮釋羅斯所主張的「初適責任」的意義,並列出其種類,然後探討他的道德理論,最後談論羅斯在當代倫理學的地位。
- 期刊
本文對價值哲學的討論,是放在中國哲學體系的價值問題中進行,並注重價值哲學體系形成的方法論問題,討論主題則設定在儒道互補的課題中,指出儒道互補是一個生活現象,應該有其理論成立的可能。而此一互補,即表現在孔孟仁義價值與老子無為價值的互補性上,並且在中國儒道哲學史中可以找出孔老二學發展線索中有仁義無為互補的理論實例,文中即說明其結合竹旳方式。就儒學體系言。儒道是以仁義為本體,以無為為境界。在老學體系言,儒道互補是以無為為本體,以仁義為次德目。至於莊子及道教老學,則因有不同的宇宙論世界觀,所以不能討論儒道互補的議題。理論上言,理想的互補形式是具備著相同的世界觀,而有價值命題的交流,使得各自的價值可以安立在對方的體系中。並且在現實生活中可以實踐出來。
- 期刊
柏拉圖的理型論一直是討其知識理論的重心,而學者甚少對他如何看待「知識」 的觀念做一說明。本文是由下列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將探討柏拉圖的右識的觀念是否類似於當知識的觀念,如笛卡兒;第二部分將討論,對柏拉圖而言,知識與理解之間的關係為何。
- 期刊
本文從中西哲學心較的角度探討了情感與理性的關係問題,認為中國哲學是屬情感型的,西方哲學為理智型的。中國哲學歷來重視情感,因為情感為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但中國哲學並不是「情感主義」,而是主張情感與理性的統一。西方哲學也講情感,但它主張情感與理性的分離與對立,重視理性的支配作用。這道德情感並不是完全主觀的、個人的或經驗的,它來自宇宙「生生之道」、「生生之理」,是與目的理性相聯繫的。情感能夠與理性統一,它本身就是通向理性的。只有可定道德情感,才能真實地確立人的道德價值。道德理性是建立在道德情感之上的,或者是由情感實現的,離了情感,無所謂道德理性。同時,情感又是靈學、宗教的心裡基礎。真正說來,情感又可分上下來說,就上而言,與理性相聯繫;往下說與個人私情、欲望相聯繫,人需要陶治情感,實現自我超越。中國情感哲學的侷限是,注重目的理性而忽略工具理性。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需要工具理性,但是必須重視人的情感問題,使人成為目的而不是工具,這才是最重要的。
- 期刊
教化一般被區分為理論性教化和實踐性教化。歸根到底,教化有著強烈的實踐性格,內涵著實踐智慧。所以,理論性教化也為著實踐的目,為實踐提供理智素質。而實踐性教化更是要對人的心靈進行塑造,促進內在精神的整體生長,幫助人成為他自己。實踐性教化有三種:職業教化、藝術審美化和道德教化。
- 期刊
本文透過對《列子‧天瑞篇》的解解,以《莊子‧至樂篇》為探討之路,說明〈天瑞篇〉實有其內在完整之義理結構。基本上來說,<天瑞篇>探討了形上思想與人生問題兩大主題,筆者認為,以上兩個主題其中有一隱態的義理結構。此一結構,簡單地說,是透過形上思想的建構作為一超越的「理據」,進而推論出吾人在形下的生活世界所應抱持的態度。 就形上思想而言,<天瑞篇>對本體論與宇宙論乃至於物化思想等形上學論題都有所措意。 就吾人對形下的生活世界所應抱持的態度來說,<天瑞篇>對生死問題、人生階段性變化及人生追求的價值都有深入的深索。

